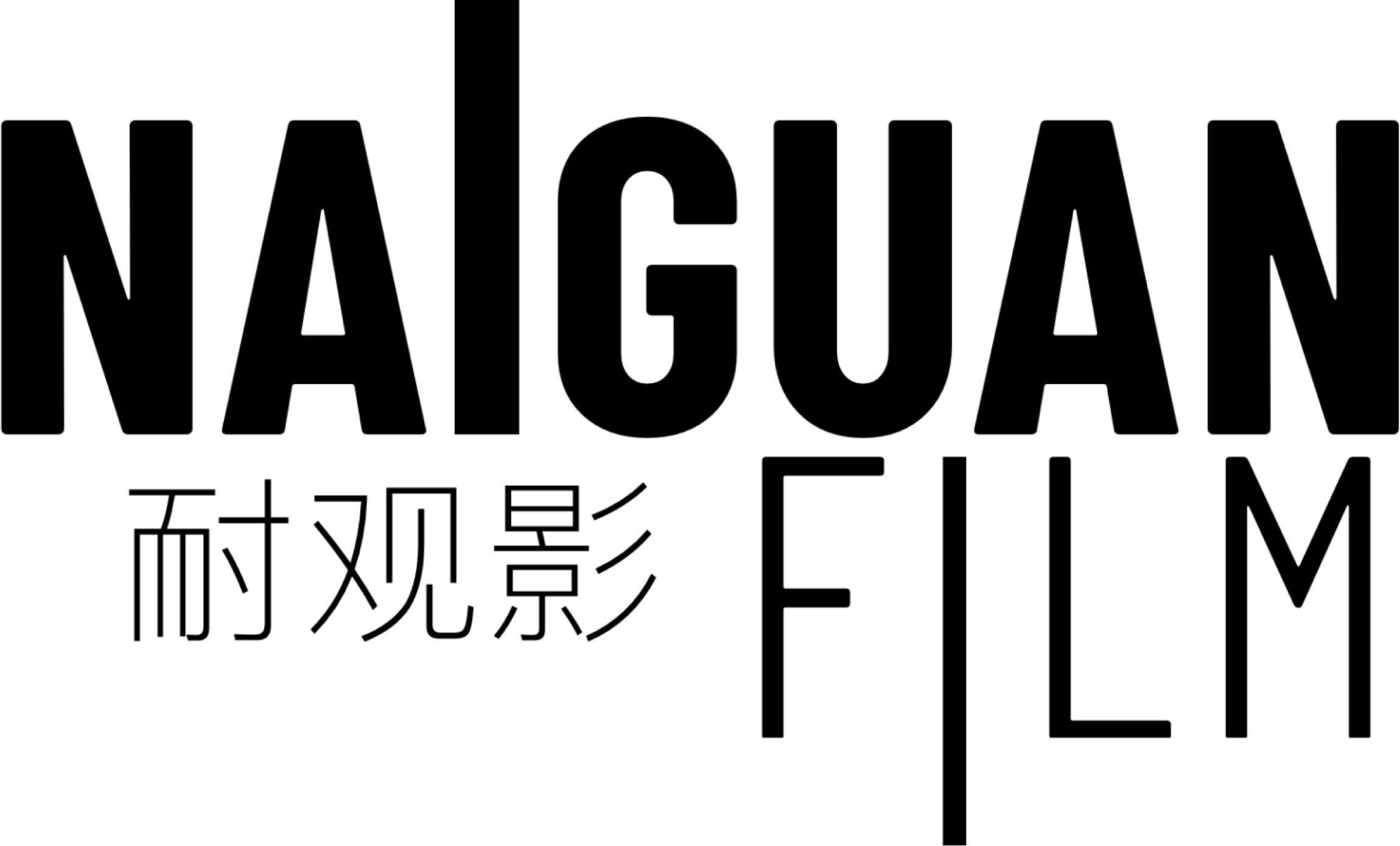本文作者 姚鹏飞
当独立电影新贵 Neon 凭借《阿诺拉》《寄生虫》《坠落的审判》等作品连续横扫戛纳、奥斯卡时,它在极短的时间内确立了作为一个顶级艺术电影发行公司的地位,以一种更加锋利的作者性和话题度抢占了独立电影的话语权。此时,我们也不禁想到曾经被视为亚文化灯塔的 A24 公司,在屡屡落下发行权的争夺战下,A24 的存在陷入到了一种微妙的境地,即它继续要捍卫独立电影的反叛底色,又不得不在大众文化流行的世界下被主流收编。
从圣丹斯电影节走出的《月光男孩》到横扫七座奥斯卡的《瞬息全宇宙》,A24 的十年历程似乎映衬着一部亚文化百年来的从抵抗到妥协的编年史——一边以坎普趣味与后现代化的叙事撕裂传统电影的规训,一边又主动拥抱着主流奖项与商业逻辑。这是一条看似矛盾十足的道路,但也应证了 “亚文化”“坎普” 的底色与真相,在流媒体时代下,独立与主流的边界是模糊的,A24 的存在,也正是当代文化吞噬与重塑亚文化的缩影。A24 的出品范围在逐步扩张,本文也将选择五部在各大电影节和奥斯卡平台上大放异彩的超现实影片作为范本来作为其较为代表性的影片序列,分别为《龙虾》(2015)、《瑞士军刀男》(2016)、《圣鹿之死》(2017)、《银湖之底》(2018)与《瞬息全宇宙》(2022)。
坎普 “显影”:亚文化的视觉抵抗与符号狂欢
A24 的崛起始于对坎普和亚文化的拥抱,从《女巫》的阴郁宗教寓言到《瞬息全宇宙》中的荒诞多元宇宙,其出品总是充斥着夸张的视觉符号以及对主流价值的戏谑。在坎普的定义中,它是一种对于传统、精英的文化标准的反叛与讽刺。坎普风格的艺术作品常通过夸大、戏仿等手法渲染出荒诞戏谑的效果表征,而其内核如同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一般,是反叛的。坎普对于流行文化有着特殊的偏好,作为大众庸常艺术的流行文化在坎普趣味的推崇下被提升至崇高的、艺术化的、戏剧性的程度。乔伊的 “贝果黑洞” 礼服、跨次元的武打戏仿、洛杉矶街头堆砌的流行文化废墟…… 这些坎普美学的典型元素,表面是对好莱坞工业美学的挑衅,实则是精心设计的“亚文化诱饵”。
苏珊 · 桑塔格笔下的 “坎普” 作为一种审美概念,指的是一种夸张、戏仿、滑稽、反叛而荒诞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文化风格,在其夸张而铺张的表征与严肃而戏谑的内蕴上对观者产生独特的情感体验。A24 也将其驯化为一种安全感满满的叛逆,这样既可以让 Z 世代在社媒上与多元脑洞相交合,有能够让电影节和奥斯卡评审感叹 “新” 的到来。这五部超现实主义电影的视觉迷宫正是 A24 所构建的割裂主流与边缘的巧妙手法。《瞬息全宇宙》中,杨紫琼饰演的伊芙琳穿梭于多元宇宙,乔伊的造型则如同坎普美学的万花筒——猫王的经典舞台造型、弗朗明哥舞裙的艳丽闪片、半哭半笑的最能反映她内心的小丑妆容,乃至 “贝果教” 的荒诞的救世主光环发型。这些戏服不仅是 Y2K 美学的复古狂欢,更是对好莱坞黄金时代戏服设计的戏谑解构。当经典被碾碎成拼贴的符号,坎普的 “不正经” 便成了最严肃的反抗宣言。

这种铺张的玩味也在 A24 的多元宇宙里蔓延,《银湖之底》让美式青年的霓虹舞池化作流行文化的坟场,亮片西装与迷幻灯光下埋藏着对洛杉矶神话的冷嘲;《瑞士军刀男》中,一具尸体与孤独者的跨性别扮演,将男性友谊的解构推向荒诞;《龙虾》则用酒店与丛林两个异托邦的冰冷对峙,将婚恋制度碾成一副卡夫卡式寓言。

坎普的 “显影” 并未局限于这些电影视觉图谱当中,《瞬息全宇宙》挪用起了香港武打片式的招式、成龙电影的动作与戏谑、王家卫的潮湿暧昧的美学与经典好莱坞的黄金岁月,《银湖之底》将玛丽莲 · 梦露的经典形象扔进波普音乐的搅拌机,黑色大丽花的报纸案头放置到古典音乐的唱机之上,A24 不遗余力地消融精英艺术与大众娱乐的界限。这种无差别的戏仿也映衬着一则后现代寓言,在宏大叙事崩塌后,一切意义都可以被消解为社交媒体上的切片,坎普成为新时代巴别塔,它既可以让人在其中狂欢,也让所有人失语。
抵抗到收编:独立电影的归顺
A24 始于圣丹斯的舞台,但二者都逐步成为好莱坞的选择秀场。当《瞬息全宇宙》以 “亚裔家庭” 的温情外壳包裹虚无主义内核时,A24 完成了一场置换——亚文化的反叛被置换为视觉奇观,批判性的话语消融于团圆的政治正确中,边缘叙事就此与大众视野融合起来。其实这未尝不是一种 “被看见” 的策略,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意义上的。

《龙虾》通过 “酒店” 与“丛林”的二元空间对峙,将婚恋制度异化为福柯式的规训剧场。影片中的单身者被迫在 45 天内配对,否则将沦为动物。此处的荒诞设定并非单纯的超现实隐喻,更是对当代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尖锐批判,同时前后割裂的空间也使得影片叙事打破了线性法则。《瑞士军刀男》则更进一步,借尸体与孤独者的共生关系,演绎了一场关乎于本我与自我的主体分裂。男性角色对尸体的女性化扮演,既是对性别规范的戏谑挑战,也是对于当代亲密关系和自我存在的深刻探讨;《圣鹿之死》则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以搏动的心脏、十字架的光影、“Exit”出口标志的多重出现与选择的隐喻隐含着对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神权的质疑和人性的质疑。

这种批判性的视觉图谱在《银湖之底》中达到顶峰。影片通过洛杉矶流行文化符号的堆砌,比如前文中提到的玛丽莲 · 梦露的经典形象、黑色大丽花的都市传说、波普音乐的历史切片等等,去构建了一个博德里亚式的拟像世界。主人公的追寻之旅映射了后现代文化中意义生产的虚无,而在《瞬息全宇宙》的叙事实验中,后现代与坎普的共谋展现出更复杂的关系。影片以极度跳跃和碎片的叙事结构和方式模拟了 Z 世代的思维认知,将存在主义危机转化为短视频式的感官轰炸,一个美式东亚家庭中的每一员的精神困境都被杂糅其中。

但是在大众文化的消解之下,其批判性也在消解。当这些视觉图谱被深度解构为符号游戏,电影的反抗也就止步于对于自身的戏仿,不是每一场独立电影制作都能变成新浪潮般的语言革新。且影片与现实中个体的生存焦虑与虚无主义也被转化为可以无限复制的文化商品,批判性思维也可被裹挟进算法推荐机制和信息茧房。这种双重性揭示了当代亚文化的困境,坎普的戏谑本是对精英主义的反抗,但在 A24 的创作框架中,它已成为缝合小众趣味与主流市场的针脚。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事与视觉奇观,在此过程中与坎普、亚文化一起完成了从抵抗到共谋的蜕变,它不再是解构权力的武器,而是亚文化被资本收编的筹码。每一时期的亚文化符号都在重蹈覆辙地被转化为可批量复制的商品,又或者是被意识形态手段重新定义。
品牌神话:符号的商品化重构
A24 的后现代主义电影以其鲜明的坎普风格,呈现出独立电影与资本博弈的复杂图景。它既置身于 2010 年代以及目前 20 年代初的美国独立电影进程中,最初的选片策略也锚定于亚文化的锋芒中,吸引了无数影迷关注。所有的坎普之姿都是在 “合法” 的情况下被搬演到大众视野当中,但这也对应了坎普本身的策略,消解精英文化,消解大众文化,而商业本身也正是要将所有纳入其中,化为可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商品,电影的属性更加袒露地暴露出来。这些虚无与戏谑的电影画面引发的观众笑声,恰恰印证了桑塔格所言的坎普的严肃性消解于 “失败的严肃” 中,反抗最终会成为一场被资本默许的行为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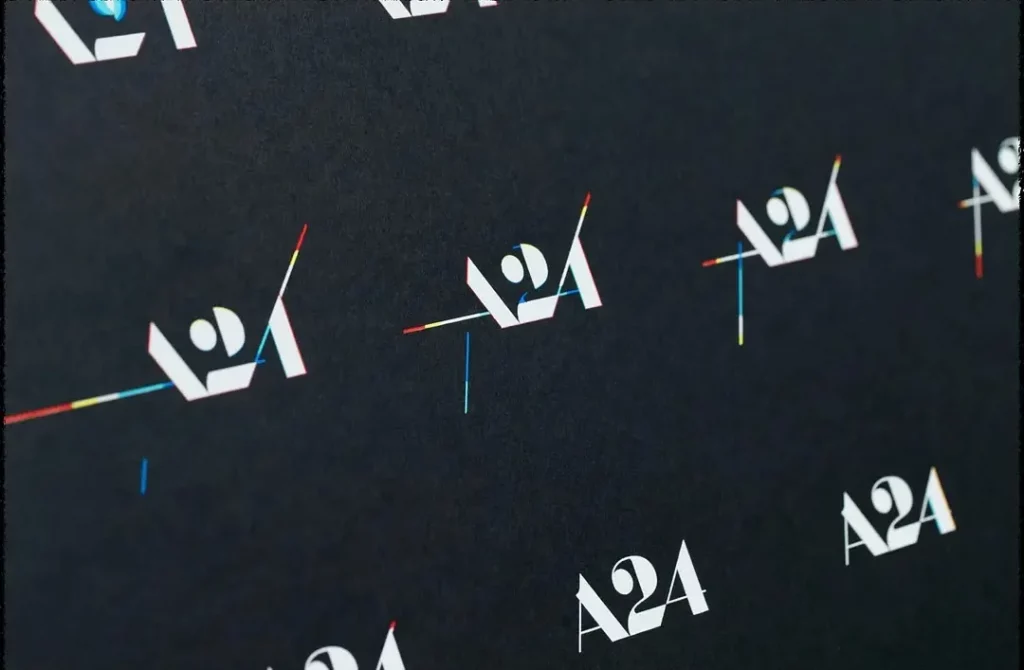
A24 的突围之路,本质是亚文化在资本浪潮中的慢性死亡。当代亚文化本身就依托于网络媒体显得更加流动与多元,它不再归属于某一个特殊的地下群体,而是成为商品化的一部分。坎普影片从圣丹斯到奥斯卡的聚光灯也证明了边缘叙事如何被主流招安,也预示了独立电影的未来:要么成为商业化的 “高级定制”,要么沦为小众圈层的自嗨。当《瞬息全宇宙》的贝果黑洞吞噬一切意义时,A24 或许也在反叛自己的初衷,那个曾以《女巫》《龙虾》刺痛观众的叛逆者,正在奥斯卡红毯上学会微笑。它也在不断扩充类型领域,延伸到战争题材的《遗军之战》,高预算传记电影《至尊马蒂》,甚至通过修复版的《Stop Making Sense》创建属于自己的音乐厂牌。“A24” 这个出现在每部影片开篇的大字,俨然从某种小众宣言变化为品牌 LOGO。当然本文的原意也并非想去批判,坎普文化的 “收编” 又或者说是合流,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进程,更何况是处于当今这个更加多元与娱乐的底色下。A24 也在扩张发行策略的同时维持一定的作者性与坎普属性,我们也尽管去享受这些影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