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法国导演科拉莉·法尔雅(Coralie Frageat)指导的《某种物质》(The Substance)如同一颗砸向每一双观众眼球的血肉炸弹,在5月19日晚间进行的首映现场掀起层层叠起的惊呼与掌声,它无疑点燃了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温不火的戛纳主竞赛单元。
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后,法尔雅在La Fémis进修一年剧本写作,随后拍摄过系列喜剧与短片作品,凭借2017年参选多伦多电影节的《复仇战姬》(Revenge)增加曝光与知名度,其新作《某种物质》入选戛纳主竞赛单元,成为角逐金棕榈的强力候补。片中的血腥场面(撕裂人皮、扎针、身体变异与器官与内脏坠落等)不断刺激观众感官感知并挑战观众的接受底线。而面对女性身体物化与性化现实的现象,影片中呈现大量同样被凝视的物化女性身体镜头,这也让法尔雅的新片《某种物质》难免陷入以“再次剥削女性形象”与“愤怒批判物化女性的社会”暧昧的影像道德难题,首映过后的差距极大的两级评论正上演着这两面观点的持续输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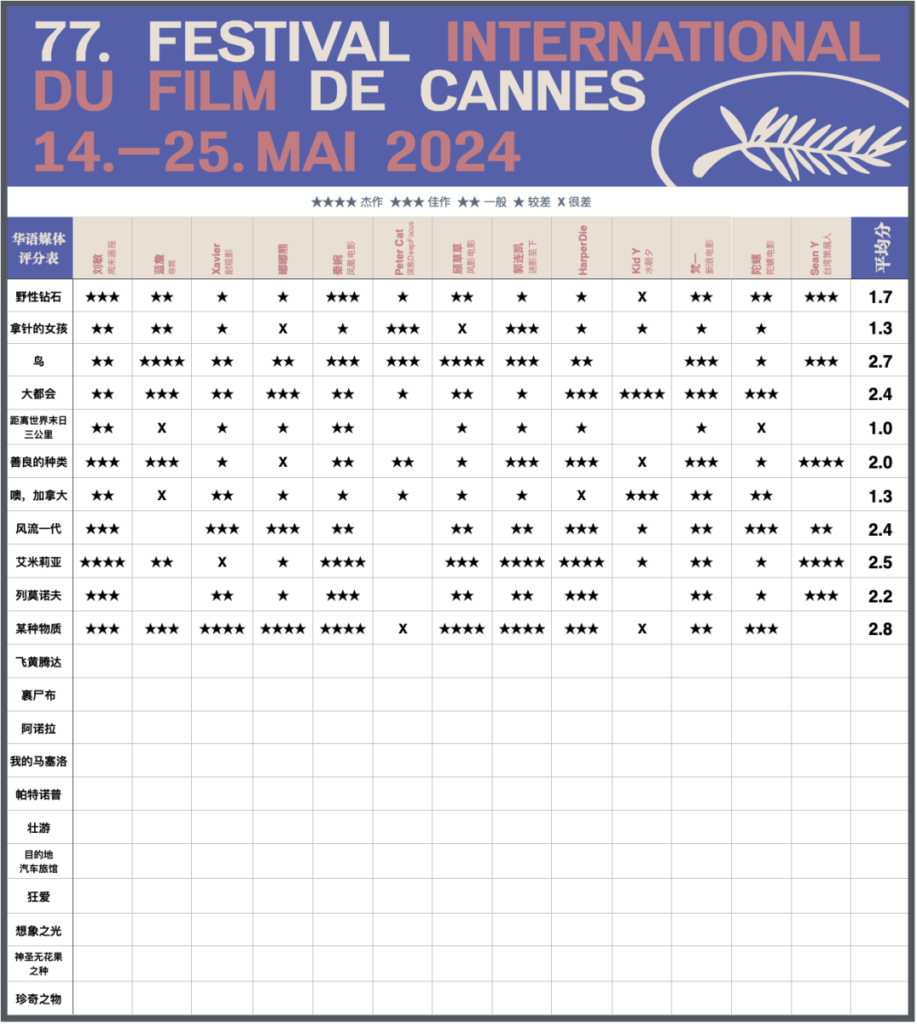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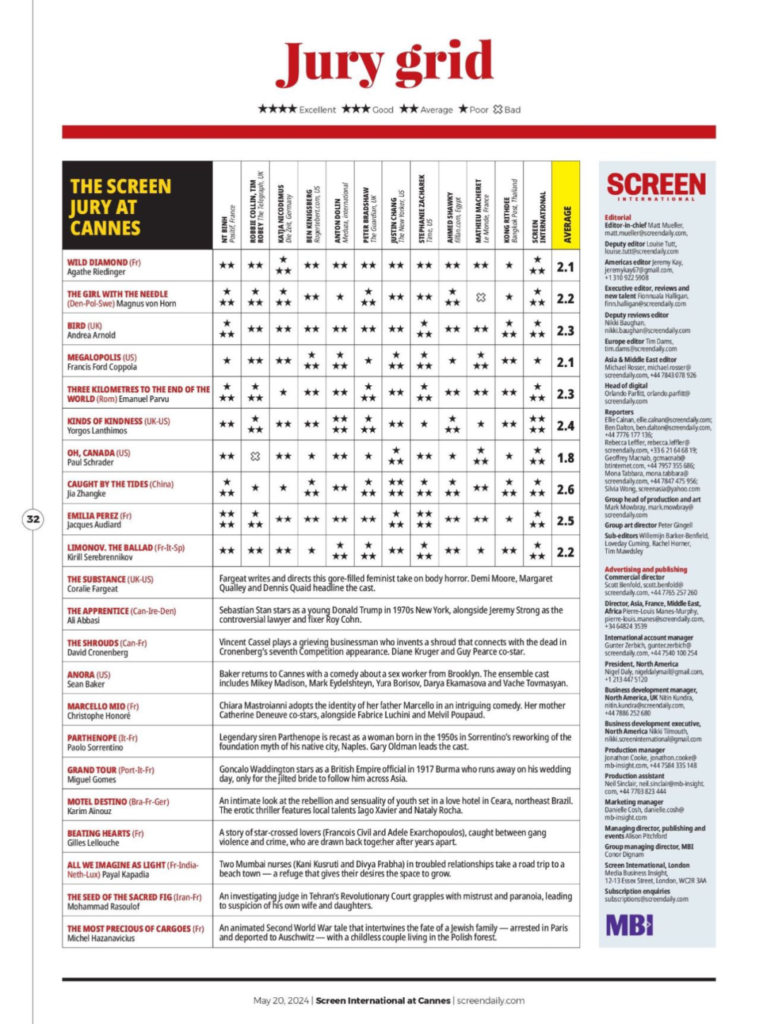
《某种物质》
THE SUBSTANCE

主演: 玛格丽特·库里 / 黛米·摩尔 / 丹尼斯·奎德
制片国家/地区:英国 / 美国 / 法国
语言:英语
《某种物质》的核心概念实际上延伸自法尔雅2014年拍摄的短片《真实+》(Reality+)。短片《真实+》中植入大脑的芯片在《某种物质》中成为名为“某种物质”的商业产品。它们都能让置入者或使用者拥有“梦寐以求的完美体型”或“一个更好的自己”,两者都将完美的形象等同于更完美的生存机会。不同的是,《真实+》从植入“芯片”的概念到巴黎外景拍摄或后期特效的制作都在努力营造一种近处未来世界的科幻感,而《某种物质》中这般并不遥远的未来感被非真实甚至或奇幻或暗黑童话寓言式的夸张所替代,并屡屡以痛感或视觉器官刺激着观众的痛觉神经,直到观众的眼球的颤抖与主角极端的执念共频为止。

《某种物质》的故事从年过50岁曾经辉煌一时的过气女演员伊丽莎白(Elisabe/黛米-摩尔饰演)说起。在面对因年龄而失去工作的危机后,她订购了名为“某种物质”的产品,企图“重生”成更好、更年轻的自己。该产品的具体运作机制是从衰老“本我”的皮囊下分裂出更年轻的“新我”,“本我”与“新我”以七天为周期交替苏醒并活动。从伊丽莎白脊椎裂缝中带着粘液爬出的“新我”是外形无可挑剔至完美的年轻女子苏(Sue/玛格丽特-库里饰演)。但随着苏接过伊丽莎白的节目并一炮而红后,苏开始渴望更多额外的时间而非回到黑暗中沉睡,于是她打破了与伊丽莎白交替苏醒的规则,无疑也违背了产品唯一的训诫“你们是一体”(You are ONE),进而引发难以想象的身体异化与荒唐悲剧。

超额的荒谬愤怒在喷射的血浆和摔裂一地的血肉混合物中被喷泻释放,观者的大脑与感知,因女性身体与血浆暴力提供的视觉快感飞上云巅。难能可贵的是《某种物质》中仍有共情或怜惜等情感触动的落脚之处,在蓝色蓬松裙摆的薄纱间,在扎入烂肉的钻石耳环反射的亮光间……伊丽莎白并非是招致毁灭的源头,她在此刻甚至是令人动容的。哪怕她以如同《铁男》中面目全非,器官各处异处的肉球行走在大街之上,她任由被灌输的欲望所驱使,导演并未嘲弄或职责她招致变异行为的决定,而是深挖置入这些执念的无形的手是谁?
影片整体的叙事结构对比前作《机械战姬》单一且明确的复仇之路有着更强的戏剧性,并构建了一个经典的三段式层层推进的结构。前作中一个一个接连被杀的具体复仇对象在《某种物质》中具象成同一女性的三种外表形态或心理状态。作为“本我”的伊丽莎白与“新我”苏产生连接并逐渐被激化,最终崩坏变异成她们合体“伊丽莎苏”的怪物形态。她们名字色彩亮眼的标题也标明着划分的节点。更要的是,女性身体变形带来的视觉恐怖与感官疼痛,以及失控的毁灭性结局,都尝试从不同细节探讨着父权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根深蒂固构建仅针对女性的,假性自然的、平面的、完美的女性形象的可怖神话。它的致命吸引力与外部社会对其的褒奖机制成为表面闪闪发光的珠宝,人人口中的爱意,名流的财富与名利,并与光滑无瑕疵的皮肤和闪闪发光的珠宝成正比。然而《某种物质》所揭露的正是这延续美丽神话的糖纸掩盖着并盘缠着女性的骇人诅咒的本貌。

William Brown(罗汉普顿大学电影学教授)在《摧毁视觉快感:电影,注意力和数字女性身体》[ Destroy Visual Pleasure: Cinema, Attention, and the Digital Female Body (Or, Angelina Jolie Is a Cyborg)]一文中提及,数字媒体时代的“真实”通过视觉与图像构成,似乎只有当一个人存在于图像中时,他才会变得真实,继而才真正存在。女性形象成为当今媒体信息与数字时代视线的焦点,也成为全体视线凝视的最终对象与被物化的商品,也是女性(特别是女明星)确认自我价值甚至是真实存在的唯一途径。这样被伪装成自然的、正确且有效的极完美形象(即呈现给镜头的真实)反衬得实际生活的样貌始终存在缺陷,始终等待被优化,焦虑在此扎根,女性对自我真实身体的态度便只剩排斥与厌恶。这加速着女性更急迫与更极端的自我物化,对追求完美的渴望(对标《野性钻石》中Liane通过整形手术等科技不断“完美”身体只为更靠近社交网络名流的情节),发展成借助物质或以技术来改善与维持自我与完美相触碰的时间的普遍现象。在此之中“衰老”则被视为失去价值与无法维持的原罪,如此岁月之于女性只剩下自我厌恶与毁灭这一条道路。

对应影片叙事,最初伊丽莎白的女明星职业生涯在面临因年龄歧视而接踵而至的过气与被解雇等危机。在机缘巧合下得知“某种物质”产品后,她未能抵挡住重回“年轻完美外形”含义下“更好自我”的诱惑。影片在此处也首次提问:签下浮士德交易的妥协是出自女性贪婪的个人欲望,还是极度物化女性形象的社会对女性提出无法逃过的要求?
最初的场景段落中,导演已然开始排列在此前采访中提及的“我想努力创造属于我的试听宇宙,一种围绕有限元素以及极度感官性的全新电影尝试。”
[ Un mise en scène taille loins, inventer mon propre univers, visuelle et sonore, faire une vraie proposition cinéma. Cinéma très sensoriel et peu d’éléments concernés. ]
为了模拟此阶段伊丽莎白紧绷的精神状态,影片开始频繁加入人物身体局部与男性面庞的特写与更多的大特写,招致观影时的压迫感与外部世界恶心感。现实生活维度中微鱼眼效果的画面不断增强着非现实的荒诞性。伊丽莎白如履薄冰般维持着的精神平衡,仍在看到自己海报的脸被替换海报的工人撕掉的一瞬间顷然崩塌,并最终在车内车外跳跃的具有冲击性的车祸镜头中完成该部分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女性形象的物化与扁平化的现象数次呈现在与(伊丽莎白与苏的)巨型海报的互动中。例如,女性富有魅力的平面海报被破坏的下一秒,无疑像诅咒般立刻兑现成女性角色真实身体的受伤;荧幕中健身节目的画面镜头不断拍摄苏局部的、碎片化的身体;以及通过反复强调巨幅广告海报中的完美无瑕赋予自身能力,而这种“赋权”实际上是我们面对规训逻辑的无力表达。当伊丽莎白意图找昔日同学重建自信时,落地窗夜景中苏巨大海报上的双眼、光滑的皮肤在短短两个镜头内代替无数诋毁的话语,又一次摧毁伊丽莎白的仅有的决心。这反应着因大众欲望扁平而逐渐形成的对“一维平面”的女性身体形象的需求,就是如此在潜移默化中向女性灌输“你们的身体要无限靠近那些一维图像中的完美现象”。便于修改,能够实现美丽如静止图片,永不改变的无法达成的要求。
在反复犹豫的内心斗争戏结束后,极其触目惊心的初次身体变异(增生)场景带着一千根针(这何不是又一位《拿针的女孩》)在毫无防备的黑暗隧道中撕碎伊丽莎白后脊的皮肤与血肉,在无法动弹的漆黑影院中猛然冲向几乎忘记眨眼的“无辜”观众。伊丽莎白皮囊之下异物的增生与其无法控制的移动游走,传递痛感与恐惧。此处有别于柯南伯格身体恐怖类型中异物的寄生或增生,此处宿主与增生者分享着身份与认知同一性,且是一种注定会因肉体分离而渐远甚至对立,且注定等待被摧毁的同一性。镜头运动与视角同样完成出色的演出,当伊丽莎白因猛然袭来的体内分裂疼痛而倒地时,主观视角下镜头立刻倾倒与旋转,紧接的有代入感的主观视角,画面中摇晃的不稳定性与朦胧视线中滴下的黏液则具身性传递着“重生”的惊悚感。
而当伊丽莎白与苏在以一周为期限相互切换着苏醒时,因对衰老身体的厌弃和对年轻外表所获得的社会追捧的羡慕,她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她们两人相继做出更极端的行为,例如打破规则的超时(不愿休眠)和放弃自我毁灭式的暴食。直到规则彻底崩坏,身体异化与暴力被推至极限,回应《机械战姬》的暴力与血浆场景随迟但到。影片不断通过快节奏剪辑、动态镜头运动与紧密笑点穿插而加强视觉吸引力,它们也许会因出现频率过高或形式的同质而被诟病成滥用或无端的重复。但片中每一处特写带来的快感/感官感知,无疑就像苏享受新生活与完美外形带来的一切名望与关注一样,是被培养的视觉成瘾性,也许不太高明但却十分有效。正如大卫·博德威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代电影中剪辑速度的增加/加强,是希望引起观众的关注并保持它。

规则彻底的崩坏带来暴力与杀戮,解决的是“本我”与“新我”之间的矛盾,但却丝毫没有撼动外界对完美女性现象需求的诅咒机制。于是影片没有停在此处,而是跟随着字面意义上“肉体不断脱落”的苏走进摄影棚,并等待最后最彻底的身体变异与冲击的来临。若说前两次变异,伊丽莎白因苏的超时而加速老化的身体和她行走的形态,逐渐让她与苏成为暗黑童话中的渴求并极度年轻美貌的巫婆与天生丽质的白雪公主。巫婆也好,公主也罢,这两个角色如同性别本身都是被构建的,是被施加的外部凝视和因社会需求而内化的规训给予的。最后彻底的变异的融合与同一,串联着早前分布在影片不起眼出处碎语中对女性外表的置评或要求。
“真是胸长在了鼻子的位置”
“漂亮的女孩就是要一直微笑”
如果作为“怪物造物”伊丽莎苏无法逃出无处不在并深入女性脑髓的规训诅咒,那它便选择全部接受,既是巫婆也是公主,胸就长在鼻子的地方,即使身体流脓,肠道拖地,也要登台微笑。
如此“怪物造物”的诚心登场却吓坏晚间表演的诸位看客,他们尖叫并粗鲁的施予暴力,影片也在此时达到血浆类型片的极致。当“怪物造物”伊丽莎苏的头颅被斩断后,血柱喷涌而出,以破坏一切的程度讲喷射的血浆洒向每一人每一处。此处颇有致敬《魔女凯莉》的毕业晚会厅与《闪灵》的走廊的视觉效果。只不过这次血浆不再淹没女性身体,而是从女性身体喷射着染红全世界。

导演科拉莉-法尔雅对待《某种物质》这部影片的身体正如社会对待女性身体一般,是物化与性化的无节制目的性使用,是残忍的肢解,是在复刻残忍的诅咒。法尔雅对《某种物质》并不温柔与节制,这也许源自于她多年来对血浆与暴力类型片的喜爱,又或者是年至中年忽然感受到社会中自我位置忽然缺失后的自疑与愤怒。若所有女性角色能如《野性钻石》中的Liane或其他逃出“完美女性形象诅咒”与“自疑自厌”的角色一样勇敢地生活,成为摆脱组走而坦率地直接地表达并传力量,也许是幸运且美好地。可现实是如同伊丽莎白一样的女性也许才是大多数,她的懦弱与自厌是如何被数千年社会结构而构建并置入到女性意识中的,才是法尔雅想要呈现的核心。
《某种物质》无疑是呈现社会机制对女性现象的完美苛求而引发的女性无法摆脱的身体焦虑与自厌现象。不断提供的视觉快感与类型化影像画面使《某种物质》所愤怒所控诉之事难敌当下的情绪与感官刺激的一次次冲刷,批判的维度被弱化也是毫无争议的事实。此外,类型片对对观众感知的刺激与强制性施虐的界限又该如何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