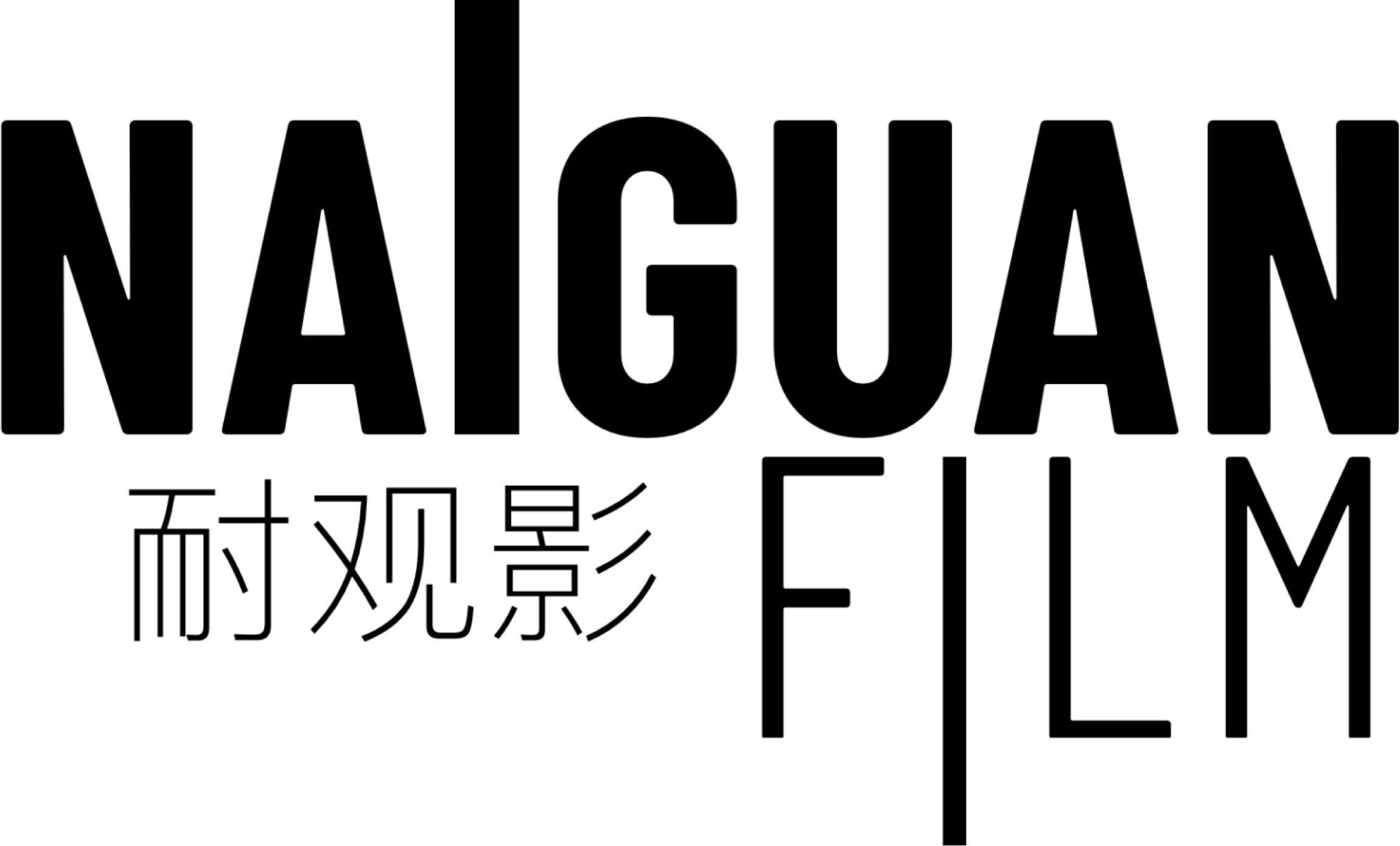前阵子伴随着第75届戛纳的落幕,国内发生了一个不算热点的“热点”:某影视博主(虽然极为牵强,但姑且这么称呼)在统计历年华语片的戛纳获奖情况时,居然错将2000年杨德昌导演在第53届戛纳斩获最佳导演奖的作品《一一》称之为“杨德昌拍的啥片名都没”,似乎是将这个片名误认为简中互联网特有的“文字消失术”。以影视博主自居,却完全不知道这一部华语电影经典作品,自然招徕了许多影迷的口诛笔伐。然而事情到这里仍未结束,该“影视博主”还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认识一部25年前的台湾小众文艺电影到底惹怒了谁?》,通篇表达的无非是对于《一一》在世界电影中的影响力的掩耳盗铃,随后还从网络流量的角度对于嘲讽自己的用户展示了优越感。此等对于自己的无知与浅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言行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由法国电影资料馆策划的杨德昌电影回顾展也于巴黎拉开帷幕,位于香港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也已于前几日更换上了《一一》的巨幅海报,不久前在戛纳展映的25周年4K修复版《一一》即将登陆法国以及香港院线。我们得以有机会重新在大银幕看到这部被世界无数影迷、乃至诸多导演所挚爱的作品——这是杨德昌导演生涯的最后一部长片,在这部影片里杨德昌少见地在一如既往的锐利中展露出了一种悠扬的温柔。其实关于《一一》、关于杨德昌,学界和评论界的讨论早已不胜枚举,那么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这样一部“台湾小众文艺电影”?

01 台北的深处:隧道、镜面与人的背面
谈及杨德昌,我们总是会想到他对于台湾现代都会中的物欲横流与心灵匮乏的反思、批判,这种表达自长片首作《海滩的一天》起、时至《一一》都一直横亘于他的影像之中。
城市的弊病作为一种超文本元素,首先依托于“隧道”式的景深构图:例如《一一》中洋洋一家搬进新家后遭遇的几次变故,像是不经意间目睹了隔壁母女的悲剧、以及重病昏迷中的外婆突然苏醒(亦或是婷婷一厢情愿的想象?)等等,人物、或者说摄影机模拟的视角都位于近段,注视着景深处的发生;还有包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经常钻进自己衣柜里的床铺去观察父亲的沦落,还有哈尼初登场时的餐厅、殒命时的马路,这样的构图在杨德昌的电影中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侯孝贤同样以景深镜头和场面调度所闻名,可二者的影像气质截然不同:侯导的景深镜头营造的是一种东方美学中的“意境”,即代表戏剧冲突的故事发生在前景,而导演真正想要传达的韵味则潜移默化地在后景浮现,例如《悲情城市》中那个经典的吃饭场景,前景的众人围着桌子高谈论阔,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议题混杂在烟酒之间,而梁朝伟饰演的言语残疾者从前景走到后景的辛树芬身旁,点起了唱片机上的音乐,二人无法对话,索性将关于感受音乐的对白写于纸上,这既是两位角色暗生情愫的伊始、又与前景的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正是侯孝贤影像中特有的历史观,一种宏观的历史与渺小的个体之间的相互映射。而反观杨德昌的景深镜头,则无不如同隧道一般,刻意将x轴的存在感削弱,人们会注意、期待“隧道另一端”会发生什么。

镜面,同样作为杨德昌影像中重要的表意元素贯穿于他的创作序列中,像是《恐怖分子》中李立中的浴室和周郁芬的书房,都通过镜子投射出了空间被赋予的人格,包括影片结尾李立中在绝望中开出的一枪,也以镜面的破碎告终。而到了《一一》,杨德昌对于镜面的使用更加娴熟,那颗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敏敏独自在漆黑的摩天大楼里,窗外的霓虹灯在玻璃上反射出她的多重投影,这时室内灯光突然亮起,原来她还在办公室,身后的同事上前沟通工作内容,这一切仿佛更加推动了她“出走的决心”。

这便是杨德昌影像中的台北,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吞噬、异化着人性,不论是隧道还是镜像,无不体现着都市的冷漠和疏离,人们的内心被自我束缚着,短视地、迫切地投入到物质上的诉求中。在《一一》的结尾,自婆婆昏迷后便再也没和她讲过话的洋洋在葬礼上讲到:“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是杨德昌少有的、在温柔中传达的寄望。

02 孔夫子之惑:失落于廉价的大时代
《一一》作为一部从NJ一家人铺陈开来的群像电影,通过年龄、性别的不同细腻地展现了身处台北社会不同人生际遇的人物缩影。婆婆重病昏迷,NJ的公司面临着转型期的经济压力,在出差的过程中与旧情人藕断丝连;敏敏感受到自我被家庭不断剥夺着,欲通过求仙问道的方式逃离出去;婷婷在结识了隔壁女孩后,同其男友展开了一段混乱的三角关系……故事在一场闹剧不断的婚礼中展开,又在一场宁静、释怀的葬礼中结束,我们得以在几个角色的人物弧光中,窥得杨德昌对于“成长”和“死亡”两大母题的执着。所谓“成长”,其实是角色“解惑”的过程,而他们的困惑通常来自于成年的甘苦杂糅中青年的憧憬;而“死亡”则更像是一种象征意味,是新旧时代的不同理念碰撞的结果。《海滩的一天》中,林佳莉面对海边打捞上来的疑似丈夫的尸体转身离去,终于得以脱离出婚姻关系的桎梏;《青梅竹马》中,阿隆意外被害于街头,在临终前脑海中浮现的是棒球比赛的画面,这是他对旧世界的无限留恋、对当今社会逻辑的无可奈何;《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劝阻小明无果、还得来了一句“我就和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的回应,绝望之下杀死了同样绝望的对方……杨德昌在对于角色的刻画中,往往将其作为时代的“注脚”,即人物一切行为的深层原因都来自于社会的影响,这便是杨德昌试图透过影像来解开的困惑:在这个愈发“廉价”的大时代,人文主义的光辉在不断失落,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还在试图通过精神对抗物质,却被社会转型的浪潮彻底吞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我想我必须要举出《独立时代》来做出更好的诠释,这大概是杨德昌作品中最为愤怒的一部,因其过于露骨的情节和导演直抒胸臆而不考虑人物逻辑的对白而遭人诟病。琪琪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表现得知书达理、颇为体面,可这种状态却招来了旁人的质疑:“你不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谈感情所件越来越危险的事吗?感情已经是一种廉价的借口了,装的比真的还像,你不觉得吗?”在一系列阴差阳错的闹剧之后,琪琪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体面”是不是真的装的了。《独立时代》,英文译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儒者的困惑。台湾社会因政治原因,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由官方推行传统的儒家思想,即便其中已有许多内容显得过于封建、保守、不合时宜。在这种思潮的耳濡目染之下,80年代的台湾又遭受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冲击,人们的精神状态随之动荡不已。杨德昌对于本土的传统思想和外来的流行文化分别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但是在批判之余,他又总是为影片中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添设一股无所适从的怅惘情绪。哪怕是孔圣人,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大抵也会产生同样的困惑。其实在杨德昌的作者谱系中,这样的困惑有着明显的情绪起伏:从合拍片《光阴的故事》中的《指望》到《海滩的日子》《青梅竹马》,那时初出茅庐、还较为含蓄,到了《恐怖分子》《独立时代》《牯岭街》《麻将》中的愤怒中夹杂的“拔剑四顾心茫然”,然后到了《一一》中,NJ出差前往日本,与商业伙伴结成知己、回国后却被告知公司因利益已决定将对方放弃;敏敏在与昏迷中的婆婆对话时陡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只关于工作、家庭,“我为什么这么少?”,带着这样自怜与怨悔,她决绝地离去、又悻悻地归来,这时的杨德昌依旧在影像中流露出了为这个社会所感到的巨大的失落,然而失落过后,他愿意为时代献以希冀——《一一》中流露出的这种希冀要远比简单释怀需要更多的勇气,这是在认清了一切真相之后依然热爱这个世界。

03 再见杨德昌:给电影人的情书
Dreams of love and hope shall never die.这句话是杨德昌导演的墓志铭,译为“爱与希望之梦永不消逝”。其实杨德昌的艺术造诣从来都无须赘述,在筹划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数次停笔,我深知在杨德昌导演的影像中、生活中所坚守的一切,是这些苍白无力的文字远远无法传达的。杨导的性格是出了名的“难搞”,他在片场会执拗于各种细节,在后期会为了剪辑权不惜得罪中影。还有一则趣闻,《一一》回母校举办台湾首映时,有记者冲到银幕前试图拍摄观众的反应,而遭到了杨德昌的怒骂、驱逐,他不希望任何人打扰观众的观影……再反观这个屏摄等低素质观影现象屡见不鲜的时代,这个追求流量、曝光而不在意真理的时代,我们重拾起杨德昌的电影,自然会与其巨大的失落同频共振。可是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电影却总是不痛不痒地假借现实题材之名,避重就轻地逃避对于现实的书写、又掩盖社会的弊病,再去冠以“温暖现实主义”、“想象力消费”、“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之虚名。写到这里又一次感到惋惜,惋惜于《一一》这部伟大的作品也成了杨德昌的绝笔,此后他在抗击病魔的过程中仅仅完成了武侠题材动画《追风》的一小段创作。我们活在愈发麻木不仁的当下,也便愈发怀念杨德昌。愿他恒常看顾那些坚持不移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