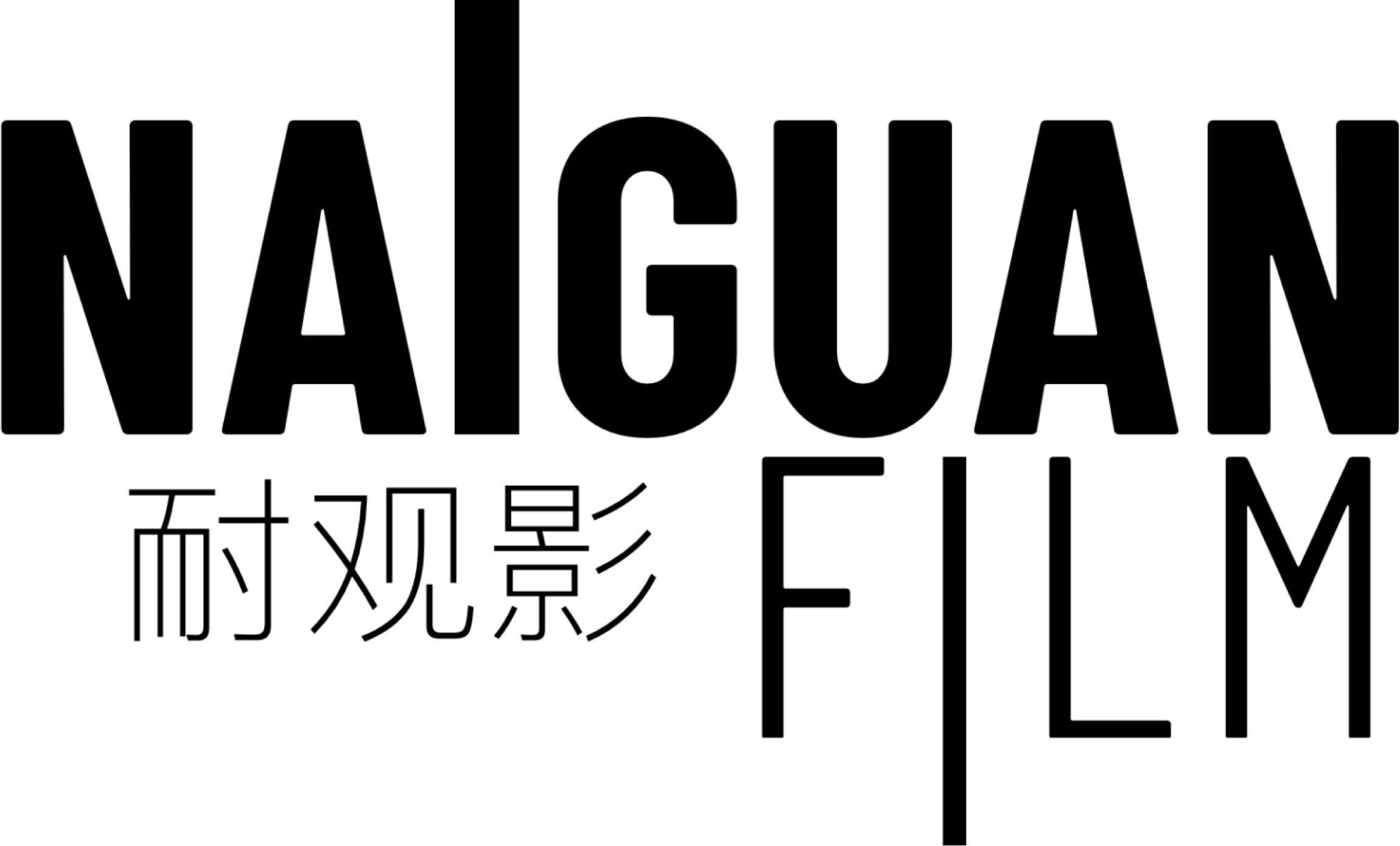本文作者 lance
黑夜的重现
黑暗的基因是不是写在了当代法国电影里?从香特尔 · 阿克曼的《长夜绵绵》,到克莱尔 · 德尼的《美国回老家》,关于黑夜的电影蔓延生长。去年法国《电影手册》十月刊便登载了关于阿兰 · 吉罗迪电影的专栏特辑「黑夜的力量」;文中写到,摄影元件的升级,摄影器械技术的发展,使得低光照环境下的拍摄的潜能被开发出来,黑夜成为当代电影的 “虚构的宝库”,黑夜变得“可拍摄”;“随着黑夜的到来,现实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所有意义。” 打开的感官和直觉,战胜了许多理性上的审美。也正如特辑中说到,光污染时代,过度的光照拓展了白天,甚至因为灯光,夜晚也成为了工作时间,人疲于生产,难以休息,独属于黑夜的感官被挤占。而电影院就像一个黑暗的庇护所,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有关黑夜的直觉。

像很多观众一样,初次观看阿兰 · 吉罗迪的电影,是要追溯到他那部拿到酷儿棕榈奖的《湖畔的陌生人》;现在想来,当时的初次观看更多地是被吉罗迪凌厉冷峻的电影风格所震撼,这部也是他的某种 “出圈” 之作,当时觉得令人欣喜的地方,是它不同于其他许多书写同性情欲的影片,而是非常规的欲望主题,在一个极小的时空内描写同性情欲里的爱恨肃杀,突破了许多在酷儿电影范畴内的常规动作,比如身份认同、恐同威胁、家庭和解,或者是情欲暧昧。稍微回溯一下 2013 年同年其他重要的酷儿电影,我们便能发现《湖畔的陌生人》的独特之处。该年就在戛纳共台展映的《阿黛尔的生活》获得了金棕榈奖,这部已经成为同影经典的三小时的作品是聚焦生活细节的都市情感写作,以小见大地刻画了性少数的当代境遇。显然,吉罗迪的创作,不管是形式上的极简,还是故事中的冷峻,都让其难成为某种流行之作;如果真要在影史上发现它的同频者,可能会是佩德罗 · 阿莫多瓦的创作,他和吉罗迪共享了许多相似性,比如情欲里的肃杀(如阿莫多瓦的《欲望法则》),以及跳跃大胆的故事和些许的幽默,就连吉罗迪本人也对此不加否认。

然而,《湖畔的陌生人》让吉罗迪首次赢得了《电影手册》年度第一影片的口碑。十余年后,吉罗迪的新作《宽恕》再次赢得了这一荣誉。也正如《电影手册》一样,我们也突然发现了吉罗迪电影里潜藏的黑夜主题。如果说《湖畔的陌生人》还算是一桩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罪行(尽管电影里最后一幕发生在黑夜),那么在前作《跟我走吧》和新作《宽恕》中,黑夜仿佛才是第一主角,是笼罩在所有角色上的绝对变量。

重看《宽恕》有两大发现,一是再次确信这是一部关于黑夜的电影——在电脑上的重看相比于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的观看,观感是大打折扣的。原因在于上述所说的,影片在黑暗中的开展是十分重要的,而电影院创作了一个完美的黑暗空间,更具体地说,许多黑暗的场景在电脑显示屏上根本就看不清楚了!第二个发现是,吉罗迪电影观看第二次的体验远不如首次,换句话说。我想原因是在于吉罗迪电影总是根藏了一种潜在的悬念,跳脱的情节开展是支撑他作品的很大力量,往往不知道故事走向会是怎样。因此,再度观看时这种悬念没有了,便失去了首次观看的那种震惊体验。
换句话说,吉罗迪一直是一位低调的悬疑类型大师。他对类型的驾驭不光是顺畅的悬念技法,而是在惯性中偶然施加的众多反惯例、反顺畅的元素;加之与阿莫多瓦类似的浮夸的幽默性,以及往往穿插的超现实梦境来搅乱线性叙事,也搅乱真实和虚假的边界(比如主角一觉醒来,而刚刚发生的一大段故事其实只是做梦),于是往往仅靠一部电影里五六个角色之间彼此的关系,便可以四两拨千斤地创造出丰富的故事张力,也可以赋予一个人物深不可见的复杂性和深度。而这样的方式在 2003 年的《勇者不眠》中已经霸占吉罗迪的影像创作,影片故事的麦高芬就是片名——如果睡去,就会不再醒来。影片有太多如真如假的情节,很难连贯成一个线性的因果。但非常直观地会发现吉罗迪对于类型的把玩。一个有些遥远的联想是,影片竟有些如大卫 · 林奇《双峰》一般的感官——小镇空间、追寻一个目标、假亦真时真亦假…… 它们共同构建起了一个永恒的时空,而在这里常常是黑夜笼罩。

简单的激情
阿兰 · 吉罗迪电影中的小镇源自他从小成长的空间,他成长于法国乡间,天主教家庭下从小接受了信仰教育,而他后来成长为不可知论的无神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但却一直对神秘主义感兴趣。在他早期的短片《老梦前行》中我们便能看见一个似乎如荒废了一般的破旧工厂,以及里面即将下岗和工人,还有初来乍到的年轻工人要来 “继承” 它们。除了影片空间秩序感极强的影像造型外,真正让我震惊的是这位导演在他的创作初期就奠定了往后的创作的基本方向,极简的调度、特定的局部时空、基本维持在五六个人物间的人物关系,潜流的同性情欲主题。意外的发现是,影迷在吉罗迪电影里观察到一种 “水平的视线”(比如《宽恕》和《保持站立》中从行驶的车上拍摄转弯时的外景,是视线的水平平移),但在《老梦前行》中,吉罗迪似乎首先是用纵深来构筑空间,光从纵深处照来,人向纵深处走去,消失在空间的秩序里,不是夕阳在窗外和工厂室内的黑暗形成对照,就是阳光把铁锈照得跟黄铜一样,了无声息的情欲幽灵像在这个工厂游荡了几个世纪。
如果说前作《跟我走吧》是吉罗迪创作风格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宽恕》更像是对《湖畔的陌生人》的复现。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之间,吉罗迪已经形成了自发独创而自洽生动的自我惯例,他是从自己创作伊始之时便坚定地自我升华、自我突破的创作者,这要求一种非常坚定的创作信念。如果说前期的创作是在风格的实验中寻找惯性和反惯例的平衡点,那么随时这种自我风格的深入,吉罗迪电影就自动参与了时代风貌的书写,从《保持站立》的相当架空和概念化 / 符号化的故事,到《跟我走吧》的介入时代和当下,这是关键的一步,他将此前的形式探索全面注入了时代内核。

在《跟我走吧》中,不仅引入了法国的移民问题 / 种族议题,还有娼妓议题、宗教问题;但却在每处都是越过窠臼,不落入某种议题电影的俗套,和不陷落在社会性思辨的二元之中。这不是一个关于娼妓的社会福祉的电影,也不是阿拉伯移民在法国受到的排挤的社会控诉。吉罗迪曾在采访中说到,与其说他的电影总是聚焦在一个与全世界独自对抗的男性身上,不如说其实是关注一群彼此隔绝的人如何试图团结在一起,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彼此。的确,正如在《跟我走吧》当中,尽管人物身份间如此隔绝,但 ta 们又是彼此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聚合的激情。就像在早期的《老梦前行》中不经历暴露的情欲,吉罗迪电影中总是在呈现这种简单的激情随时流淌而出。在《湖畔的陌生人》或是《保持站立》中,这会招致绝对的灾难,呈现着人被自己所欲求的东西所掀翻的绝境;而在《逃亡大王》《跟我走吧》以及《宽恕》中,则是呈现这种激情如何突破了人因自我的信仰而自我奴役的局面。
色情的遗志
就《宽恕》来说,这个主题更显具体,片名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专有名词。如上文所述,阿兰 · 吉罗迪是成长于天主教家庭而后成为不可知论无神主义的,具有某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性恋导演,这些标签叠加起来像极了另一位电影大师,意大利导演皮埃尔 · 保罗 · 帕索尼里。曾有采访问到吉罗迪,《宽恕》是否是对帕索尼里名作《定理》的致敬,毕竟两者有不少的共同之处:男主角来到一个小镇 / 家庭,受到偏爱,搅乱平静。吉罗迪本人予以否认,他认为正如同 “定理” 一片名一样,帕索尼里显然更直接针对信仰这一主题进行辩论;《宽恕》相比起来显得更轻盈,更暗流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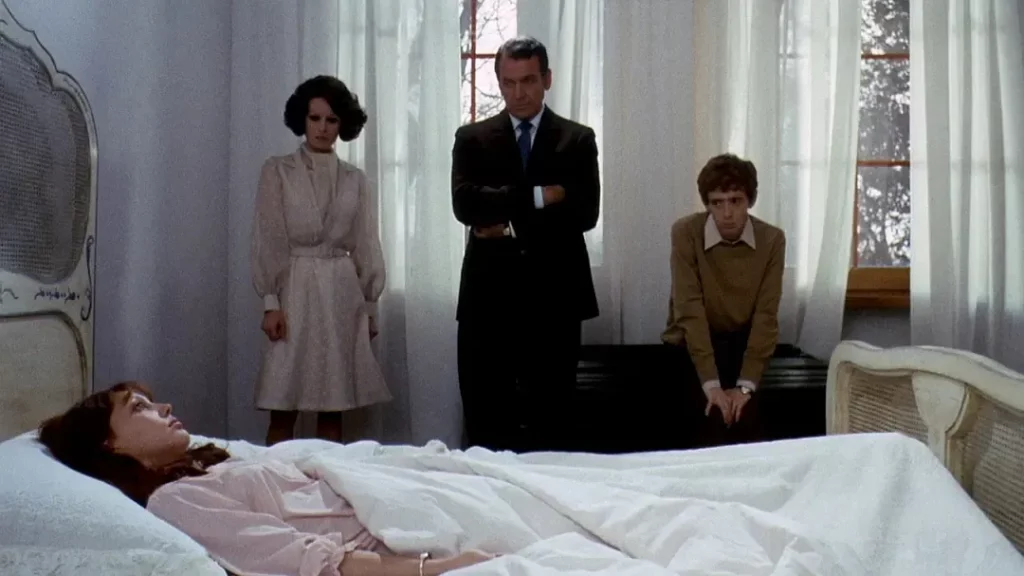
显然,今天的严肃的同性恋导演仍需要活在帕索尼里、法斯宾德、阿莫多瓦的阴影 / 遗志之下。在此并无意进行比较,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确有这样的遗志继承,那么重要的便是它在今天所揭示的时代议题。如同影片中神父说到,谁要为历史负上罪责,是否每个人都是他人灾难的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因此我们如何宽恕自身?
一个具体的切口便是,吉罗迪电影显然和当下风行的身份议题电影拉开了十足的差距,前者关注聚合,而后者揭示割裂,并躲藏在一种身份的道德正当性的光芒下,它背后的阴影是全面否定了此间的流动性,而固化为彼此间的对立。同为 2024 年戛纳电影节舞台上的《艾米莉亚 · 佩雷斯》仿佛是这样的绝佳例证,它也惊人地在欧洲电影艺术和美国奥斯卡学院奖的双重电影评价体系下都获得认可(于此同时是吉罗迪在各种评价系统中的边缘地位,除了《电影手册》)。这倒不是单一的世界电影评价体系自身出现了问题,而是更宏大的,诸如苏珊 · 桑塔格的 “色情艺术学”,或是吉罗迪本人所喜爱的巴塔耶的色情学在今天被泛化为了在商业消费上的放纵的正当性,可能更耸人听闻地说,这是“批判” 本身变成了 “景观” 的社会危机。
尽管吉罗迪本人对此不加肯定,但我们真的在他的电影中发现了帕索里尼的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