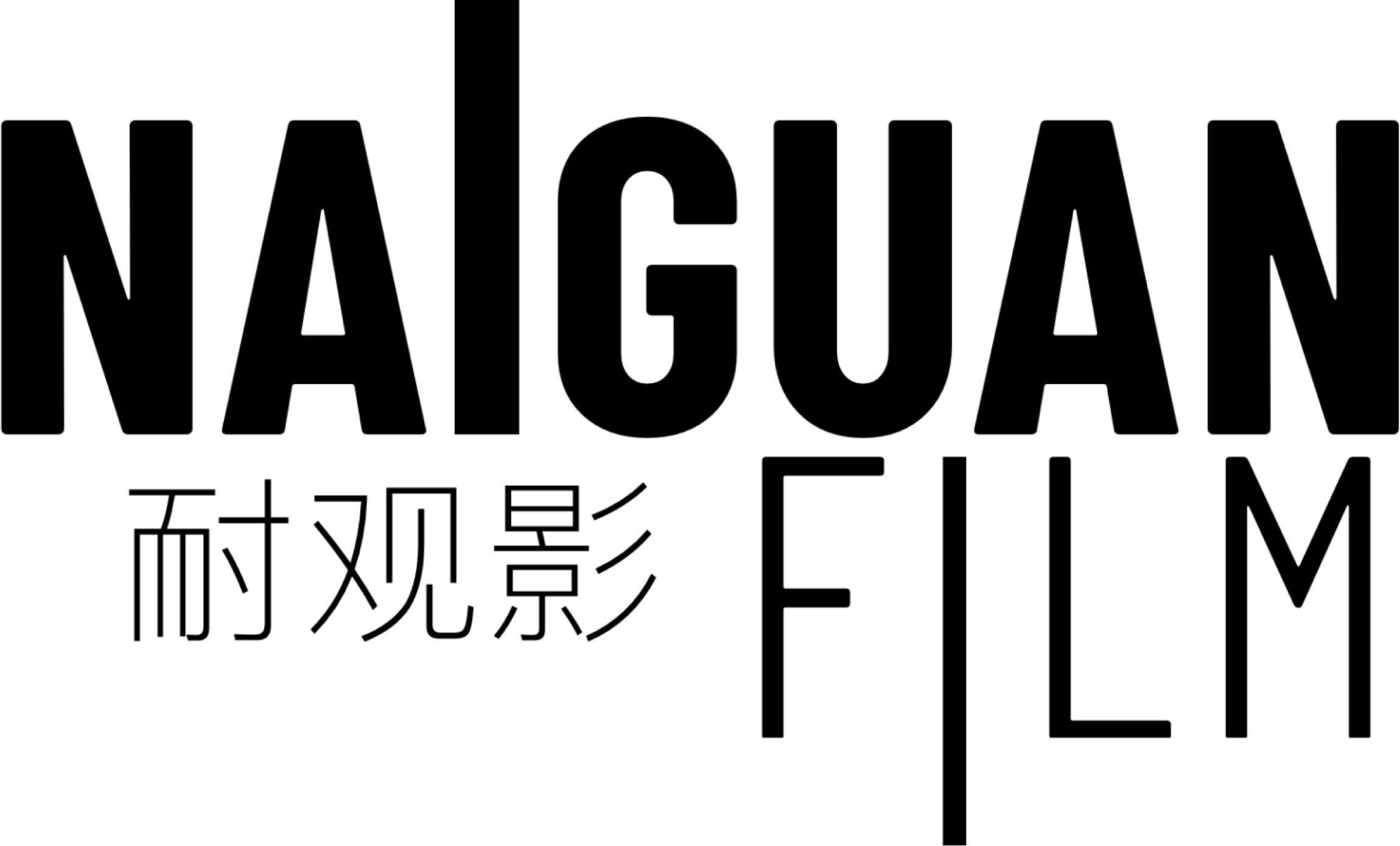有这样一部犯罪片,启发了奉俊昊的《寄生虫》,李沧东的《燃烧》,今年还被斯派克·李翻拍了新版。然而,它如同梅尔维尔的《红圈》、布列松的《扒手》一样,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它就是黑泽明的《天国与地狱》。
「 设计的真实 」
黑泽明的电影,总有一种精心设计的真实感。这一点在《天国与地狱》这部犯罪刑侦片中尤为明显。
影片有着明晰的两段式结构:前为“天国篇”,以富商权藤为中心,讲述权藤面对绑架案的内心挣扎;后为“地狱篇”,以警探户仓和罪犯竹内为中心,讲述破案与抓捕的全过程。
影片的前54分钟没有场景切换,全部发生在权藤家的客厅内。有限的空间如同室内剧的舞台,黑泽明仅靠构图与调度、灰度与光影、演员的肢体语言,成功刻画出了强烈的戏剧冲突。
在开场的国民鞋业高层会议中,权藤以一个坚持制鞋理想的硬汉形象出场,不满于公司的老人政治,意图并购股权完成夺权。紧接着儿子突然被绑架,但马上发现绑匪认错了人,错绑成了司机的儿子。绑匪依旧索要赎金,而金额正是并购股权所需的数目,让权藤陷入两难的境地:是拒绝支付赎金保障事业,还是牺牲事业挽救司机的儿子。
权藤不仅被置于道德困境的中心,也成为调度的中心。他永远占据画面的重心,处于最亮或最暗的为之,吸引观众的视线,也牵动着其他角色的注意力。黑泽明对构图中的高低位置关系有一种特别的执着:让更多的角色同框,并借由位置关系来表现角色间的权力关系。权藤反对支付赎金的时候,他占据画面的上部,俯视画面底部的其他角色,主张个人自由,拒绝道德绑架;而在他转变态度、同意支付赎金之后,角色的高低位置反转,权藤成了唯一位于画面下部的人,其他角色站立着,但低着头,沉默中是对权藤的同情与惋惜。




接下来,黑泽明仅用了短短8分钟刻画赎金交接的紧张段落。先前作为悬念的交接方式,此时水落石出:权藤需要将7厘米厚的手提包,在列车驶过酒匂川铁桥的时候,从二等车厢卫生间那只能打开7厘米的窗户里扔下去。在运动的火车上全程手持实拍,这意味着极高的NG成本,观众也不由得提心吊胆。手持镜头的抖动,演员的不安,一切都在飘摇之中,将紧张气氛推向高潮。

将孩子平安赎回后,户仓警探的破案过程,更是设计与真实相辅相成的范例。刑侦段落的开篇,便是由都市景象叠画而来的一张东京地图。接下来的办案过程,一如这张地图一般严谨而清晰。

在这里,黑泽明用了很多群像镜头,呈现出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体系截面。如此群策群力、尽职尽责、有人情味的办事过程,今天的观众看了也要叹为观止:警局内短短的汇报会上,地图组、列车电话组、当事人闻讯组、乙醚组、轿车组、纸币追查组、大众信息收集组、铁路组、犯罪动机组轮番汇报,有效信息迅速整合。警员们不断摇扇、擦汗、大汗淋漓,让观众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热的不行,也暗示着案件进展十分焦灼。
不仅体系内部如此高效,整个社会面上各种人群也都特别给力。警员们相当投入,即使在休息时间也反复重听通话录音,最终听出了铁轨声,由此破获罪犯所在位置的关键信息,让案件由暗转明。媒体记者们也团结一致,配合警局散播消息,诱捕罪犯上钩。普通市民也非常同情权藤的遭遇,热心贡献目击情报。




警局由这些信息,迅速将孩子被绑期间的关押地点锁定在了江之电铁路沿线。观众跟随警探,来到泥泞的鱼市,来到镰仓刚开发的别墅区。精密设计的破案线索,在全程的实景拍摄下变得十分可信,仿佛绑架案当真曾在这里上演。



最终,报纸记者们的配合起了效果,罪犯看到赎金已被追踪的新闻,慌乱之中丢弃了装钱的手提包。手提包中预埋的化学物质,在焚烧炉中冒出粉红色的烟雾,彻底暴露了罪犯的所在地。黑泽明用胶片手工上色的方式,创造了这部黑白片中唯一的彩色,标志着案件突破性进展,为警探和权藤燃起希望的曙光。

「 天国与地狱 」
权藤那建在山顶的别墅气派豪华,宛若天国;而臭水沟旁的底层社区泥泞不堪,热得像地狱。这无疑是贫富悬殊、阶级分化的直接呈现。年轻的见习医师竹内,从他地狱般的狭小出租屋里,窥视着高高在上的天国,仇富成为他犯罪的动机。

其实,即使在权藤那“天国”般的豪宅之内,也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区隔。
司机青木是底层。尽管青木才是真正的当事人,但一直是权藤在把握着主动权,牵引剧情、摄影与情绪氛围变化发展,青木始终徘徊在画面的边缘,被排除在决策制定的圈层之外,毫无话语权。他无法掌控自己与儿子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富豪的善良恩惠,取决于权藤的一念之间。
权藤是上层,却并非最高层。权藤的债主们才是真正的资本家,而权藤是实业家,有着一种近似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情怀。影片的第一幕就是从权藤家那宽敞的落地窗看向东京的人间烟火。这落地窗仿佛权藤心中对社会底层保留的一种情感联系。心怀歹意的竹内得以藉此窥见权藤,权藤也藉此有勇气完成阶层降落,或曰回归。



警察的位置更加微妙。在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的社会中,警察不属于“地狱”,也融不入“天国”,而是扮演着旁观者、调和者的角色。作为旁观者,户仓和“水手长”两位警探对竹内的态度从无感到憎恶,对权藤的态度则从疏远转向敬佩和同情,隐含着本片的价值评判。作为调和者,警察只能完成惩罚犯罪的基本职能,而那真正的“地狱”——滋生犯罪的社会现状,却是警察无能为力的事了。


随着竹内的视角加入叙事线索,真正的“地狱”展现在观众眼前:繁忙的港口泊满货轮,酒吧里塞满美国大兵,黄金町“毒品街”上毒虫形容枯槁。正如那豪宅倒映在水中的镜头所隐喻的:日本60年代的经济腾飞仿佛水面倒影,而水体本身藏污纳垢,泥泞不堪。社会的失序,精神的疲软,始终存在于经济发展的阴面。

「 国际的黑泽 」
都说“国际的黑泽,世界的三船”——黑泽明的国际性是双重意义上的。一方面,黑泽自身的文化基因就是高度国际化的:他爱夏加尔、梵高、塞尚的绘画,爱约翰·福特、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也翻拍莎翁和陀翁的作品。《天国与地狱》本身的剧本也改编自一位笔名Ed McBain的美国作者的侦探小说King’s Ransom。
另一方面,黑泽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天国与地狱》所探讨的问题,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问题,也几乎是所有受到美式资本主义入侵的文化社群所共同遭遇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天国与地狱》的故事跨越60多年,放到韩国社会或者美国黑人群体的背景中,依旧能震动人心。
黑泽明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其实早在其战后作品中就已经出现。1948至1949年,黑泽明拍了三部战后“教育片”,以病患(《泥醉天使》《静夜之决斗》)或罪犯(《野良犬》),隐喻美国占领时期失序的社会。《天国与地狱》中的酒吧让人恍惚置身于美国,唱片机放着爵士乐,人们忘情地跳着摇摆舞。类似的情景在《泥醉天使》也有呈现,女舞者跳着野蛮而全无章法的舞步,唱着一首Jungle Boogie:“我是母豹”。女舞者的扮演者,正是当时凭借《东京boogie woogie》红极一时的歌星笠置静子,而那首黑泽明亲自填词的Jungle Boogie,将来自美国的爵士乐表现为猎奇的、野蛮的、高度娱乐化的,暗含着对美国流行文化入侵的指责。


与此同时,黑泽明通过设置医生、警察作为病患、罪犯的对照组,强调内部归因和个人选择,呼唤理性与道德。《天国与地狱》中,权藤与竹内都出身自中下阶层,竹内出于仇恨走上犯罪,权藤却选择舍己救人。《野良犬》中的警员与罪犯都是退伍军人,都在复员回家的路上被人偷了包,罪犯由此决心报复社会,而警员却由此决心加入警察队伍改变社会。黑泽明试图将命运的选择交还给每一个个体,并许诺了“善有善报”的结局:使人得到同情与尊重的,并非因为财富和社会地位,而是个体的道德选择。



对于“地狱”中的人们——无论是经济阶层中的底层,文化秩序中的堕落者,还是道德阶梯上的自暴自弃者,黑泽明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持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天国与地狱》中,这份同情集中在了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竹内身上。竹内初登场时,摄影机尾随他经过那臭水沟,然后固定在巷口,目送他步入棚户区的深处,没入黑暗,走上犯罪的不归路,似乎含有一种同情的注视。影片结尾处,权藤看向竹内的眼神中写满哀伤,也是在为竹内的遭遇和结局感到心痛。

然而,不同于战后时期的作品,《天国与地狱》不再有那么强的说教意味,而是多了一点反思。结尾处权藤与竹内对话过程中,玻璃窗的反射让两人的脸同框、重叠,意味着两人之间同根同源,阶层之间的沟通对话、相互理解也依旧可能。然而最终,铁幕落下,权藤只有对着自己的虚像沉默。权藤和竹内的本质不同被揭示出来,同时也意味着跨阶层的沟通仍旧困难重重。权藤大可以施以悲天悯人的同情,但他的怜悯只能照见自己,他无法挽救竹内的灵魂,也无力改变社会。

《天国与地狱》尽管是一类犯罪片的原型之作,却包含了太多无法被“犯罪”“刑侦”类型标签所定义的内涵。本文也仅仅罗列一二,那些精妙的情节和调度设计,只有在反复重温中方可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