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做到让我们对一个宣称自己是坚决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女主角产生如此强烈的同情心的呢?
这个问题很直接!其实,《亲爱的同志》可以看成我的电影《战争天堂》的镜像。主角是一个正直的纳粹:他喜欢契诃夫,会说俄语,会弹钢琴,英俊得如同天使,充满贵族气质,绝对无辜,同时也是……一名纳粹。

面对这种性格交织的人物,可以预想他的结局会很糟糕。问题就在于此:展示生活的矛盾性。但在艺术创作中,这很难,因为观众往往期望被告知谁是好的,谁是坏的。我想让观众来决定并做出道德上的选择。
我很高兴你没有把这部电影看作反斯大林主义或反苏维埃的控诉,而是看作一部拒绝把矛头指向好坏的作品。想一想麦克白:他并不是一个好人,麦克白夫人则是一个女巫!但在所有对麦克白的伟大诠释中,例如黑泽明的《蜘蛛巢城》中,他被视作一位君王。想想他是如何面对死亡的……这个角色身上的双重性是非常奇妙的。

在《亲爱的同志》中,你刻画了一个正在崩溃的体系……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永不崩溃的体系给我看,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薪水都给你!我认为腐败是人之本性。当我筹备《战争天堂》时,我想寻找两个演员来扮演纳粹分子。但即使在有薪水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西德演员愿意试镜,而许多东德人却愿意扮演这些角色。
西德地区仍然有负罪感,就与纳粹毫无关联的年轻人也不愿谈及此事。在影片中,集中营的负责人说,一个没有腐败的世界将是完全没有人性的。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悖论,但事实的确如此。腐败指的是出于自己的情感和个人利益而违反法律。俄罗斯人在这方面很出色,意大利人也是如此……
你为什么选择用1比33画幅的黑白电影形式?

我无法想象《亲爱的同志》是彩色的。看到彩色的革命影像是愚蠢的。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影像资料都是黑白的;那个时期的大多数电影也是如此。
制片人们想要把《亲爱的同志》拍成彩色的,他们的借口是如果不这样做,年轻观众就不会去看这部片子,我们就会因此失去很多利润。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拍成彩色的,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很假。我能理解年轻人不想看黑白电影,比如费里尼的黑白电影,因为他们觉得它们娱乐性不够。
艺术可以提供娱乐、教育、知识……但我想通过电影传达我的思考,而不是只提供消遣。我试图让观众进入情感的涌流中。你看了前三到五分钟后,就不会再考虑画面黑白或彩色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深深相信了银幕上所发生的事情。
对我来说,艺术能让人们重新回到弗洛伊德定义的童年时代:童年,是信仰。这个定义可能不太符合你们法国人的笛卡尔思想……

我期望从观众那里得到的主要情感,是他们看完电影后的沉默不语。这沉默代表了我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时刻。观众们不明就里,因为他们可能已经被电影的故事所触动,随之产生了情绪波动。这就是艺术的精髓:观众感谢你,是因为你让他们在一小时四十分钟内与童年重新建立了联系。艺术来自于肺腑,来自内心。之后,想法就成形了。
选择黑白的画面,是不是也能跟片中大屠杀的惨烈保持一定距离?
坦白说,现在的我拥有拍摄的绝对自由。当然,我必须得有一个有钱的合伙人,就像米开朗基罗有他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但是,这不是一个与制片人的商业交换。不是说制片人给了钱,就要获得相应的回报。在今天,艺术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资助的。但我之所以创作,不是为了让有钱人买回去、挂到家中墙上,作为某种投资。洛伦佐·德·美第奇付了钱,但他并不转卖自己购买的作品。我和我的制片人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cher Ousmanov)正在朝这个方向上努力。

《亲爱的同志》是我继《罪恶》和《战争天堂》后第三次和乌斯马诺夫合作。他是相当有勇气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要求我回报他的投资。我向他解释说他的钱有可能回不来,他完全接受。有许多别的制片人来找我,但一听说他们一分钱都收不回去,扭头就走。
你在重现60年代时遇到哪些困难?你在哪里拍摄?

在拍《罪恶》时,为了重现佛罗伦萨,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城市搭了景。《亲爱的同志》也是如此。每次拍摄时,只有部分拍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幸运的是,我从来不拍300度全景,只在一个方向上取景。这给布景师省了不少功夫。我的经验很足,我可以拍得少,同时保证镜头始终充满力量感。熟能生巧嘛。
你是如何创作剧本的?你在哪里找到这些历史文献的?
写剧本不是艺术,它与场面调度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研究文艺复兴、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还是《奥德赛》,我都会深入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花上十年也可以。《亲爱的同志》的想法是在我读到一本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新切尔卡斯克惨案,或称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苏联军队和克格勃官员于1962年6月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屠杀*)目击者的回忆录时产生的,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还在世。然后,我转身去拍了其他电影……
第二次冲动是我在剧院指导我的妻子尤利娅·维索茨卡娅(Ioulia Vissotskaïa)时产生的。她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扮演安提戈涅(Antigone)。尤利娅是一位出色的悲剧演员。我喜欢她表演中的狂野能量。创作悲剧比创作正剧更难,因为正剧拥有逻辑,悲剧则基于一种非理性的力量。顺便提一句,我的第一部电影《第一位老师》,我就是把它当作一个悲剧来拍的。

在《亲爱的同志》里,我的灵感是美狄亚(希腊神话中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我把柳达这个角色视作一个信奉斯大林主义的狂热分子。她原来是一个纯洁、善良的人,但又像所有狂热分子一样盲目。这种盲目给了她力量。

然而,影片的第一个小时却充满了讽刺意味:官僚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观众则在嘲笑官僚们令人困惑的处境。
你关注的点很有意思,因为整个第一部分都来自于历史记载,我只是把那个时期的真实记录写进了剧本,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我的原本意图并不是使这第一部分充满讽刺性,我只是想展示那些官僚——那些坐在那儿、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不幸的人们。

柳达是唯一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只是在装模作样。结果这变成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而我一开始还觉得“谁会对这些克格勃成员(KGB,指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互相质问谁射杀了谁的无聊讨论感兴趣?”从症状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能意识到其中涉及的哲学和心理问题,斯大林时代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每一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都是一本迷人的读物。
我们能否将最后一幕解释为一个梦、一个月光下的幻觉?
我不想向你解释。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会告诉你,你说的没错……我更喜欢让观众们自己思考。此外,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生活中非理性的部分永远来自于奇迹。所有的信念都是非理性的,但失望可以是理性的。对我来说,保留人类身上非理性的这一部分,十分重要。
在《亲爱的同志》的开篇,你展示了柳达在通奸后的半裸镜头,而电影此后的画面中渐渐不再有裸体了。你是想借此表达那个时代的妇女是自由的吗?
我避免将这些事情合理化。首先,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她和别人睡觉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苏联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正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展示的那样。性在苏联人生活中是自由的升华。最自由的性生活不是在瑞典,而是在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 但这个场景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我可以用巧妙的解释来证明这一点,讨你欢心,但我不想花言巧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有这样的印象:我不停地回到过去,却不甚了解我所做的、所写的和所拍过的一切。我只知道我是这么过来的,不论对错。
你成功地从非常平凡的影像中汲取到了诗意,比如道路上的沥青。
这是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当局重新铺设了街道上的沥青,以消除大屠杀的所有痕迹。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当年的文件足以佐证当时可怕的时代背景,甚至片中关于舞厅的轶事也是真实的。在当年的苏联,跳舞跳到凌晨三点是几乎无法想象的事情,十一点钟时,一切都得结束。
我喜欢这些细节。直抵事物核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成为观众注意力的焦点。我对人物行为的周围环境、那些无用、但能让我们接触到真相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例如柳达蜷缩在浴室里向上帝祈祷的场景。很明显,这个片段是我虚构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决定:我决定让她不在教堂、而是在厕所里祈祷! 她吟唱的苏维埃歌曲也是如此。

这首歌出自哪部电影?
出自歌舞片《春天》。该片在斯大林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部由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Grigori Alexandrov)指导的电影,他曾是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助手,是一位重要的导演。我爱这首歌的旋律。此外,我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是我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Sergueï Mikhalkov)写的。我事后记起,当时是1947年,我和祖父在乡下,父亲在看完该片的首映后来找我们。

当我想到柳达可以在跟克格勃成员在墓地的对手戏之后唱这首著名的苏联歌曲时,我只想对自己说,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我于是向我的妻子解释,当她在片中发现她的女儿被埋在那里时,她应该唱这首歌。我妻子答道:“什么?你疯了吧!”
对我来说,这段情节以一种奇怪而充满悲剧性的方式产生了意义。柳达由此上升到了绝对的绝望,这就像量子飞跃,我们进入了第四维度。悲剧总是把我们带入第四个超维度空间。
你在影片中增加的另一处虚构的细节是柳达从远处观察马匹和年轻人的场景。这个镜头的精妙之处在于,我们与这个场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换做一个糟糕的导演,他可能会给直接给我们来一个特写镜头……
你说得很对。但是,我想再次强调,解释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 你知道,倒影有时比光本身更强。在倒影中,有一部分的……折射(法语中“折射”和“反思”是同一个词réflexion*)。我们能想象的比我们能展示的丰富得多。电影的影像是一个粗暴且粗俗的东西,因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看到一切。为了邀请观众进行深入的思考,我们必须为他们留下想象的空间。

在《处女泉》中,当已故的马克斯·冯·西多(Max von Sydow)——他也是我的一位密友——质问上帝为什么让他想要杀死牧羊人时,伯格曼是从背后拍演员的。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让观众看到粗俗的画面。伯格曼和布列松一样,是留白的艺术大师。布列松曾经说过:“展示什么,不展示什么,不能搞错,特别是不展示的部分。”
在写《亲爱的同志》时,我尽量不写下那些太渴望被拍摄和展现在屏幕上的元素。我剪掉了所有超出了单纯暗示的镜头和场景。我经常同时从几个角度拍摄一个场景。但当克格勃成员去警察家时,我只拍了一个镜头:我拍了三个成员的背面。我们看不见那个女人,只看到婴儿的脚,但我们已经明白了一切。在电影中,一帧简单的图像也可以是无价的。但是现在的导演都在试图将画面放大。你能告诉我,当一张一百美元纸币就足够时,一百张一元纸币或同值的两公斤硬币有什么意义吗?
我现今的目标是某种极简主义。这种极简主义,15年前的我是无法实现的。2014年我拍了《邮差的白夜》,从那时起我便开始钻研影像的隐喻力。每拍一部电影,我就学到一点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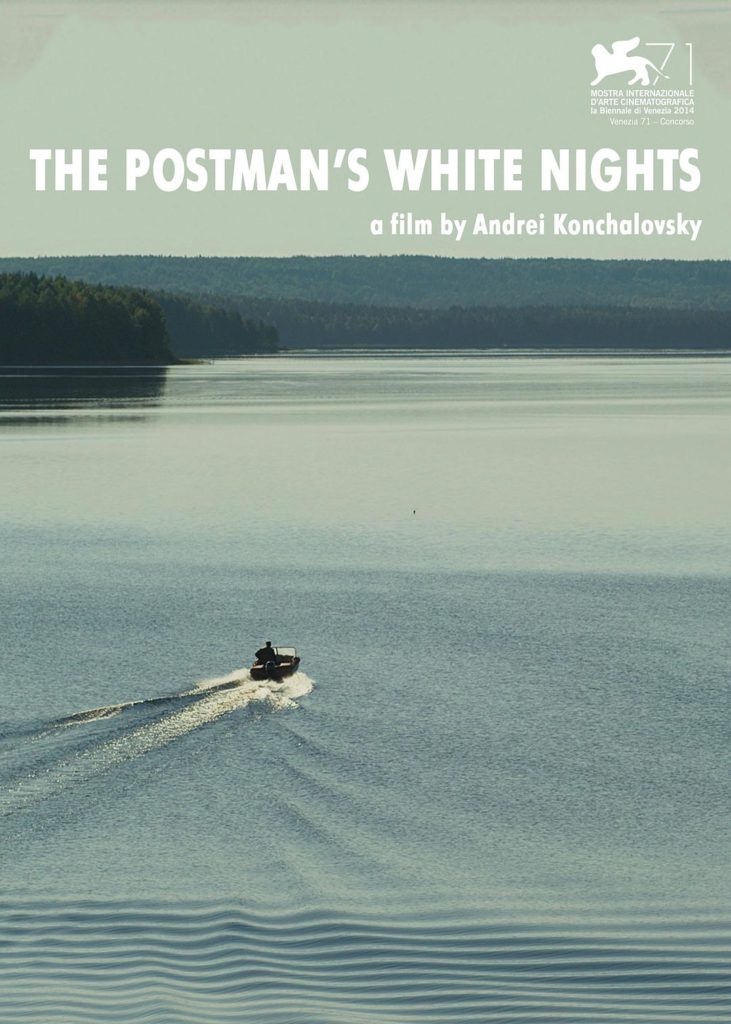
影片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四十二天拍摄,三周剪辑。
可是没有人能在短短三周内就剪完一部电影!
如今我们的工作方式与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需要打光和排灯。在以前,像我这样的导演会跟运镜师谈好几个小时,无休止地讨论视角和构图。而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存在了,被iPhone抹杀了。在今天,一部电影的美,跟谢尔盖·乌鲁舍夫斯基(Sergueï Ouroussevski)这样的摄影师在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ïl Kalatozov)导演的《雁南飞》中所做的工作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

如今,最重要的是准备工作。为了拍《亲爱的同志》,我花了很多时间来选择面孔,悲伤的面孔,苏维埃的面孔。然后是服装和视觉氛围,接着,我让女主角工作。她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能够诠释一切角色。她的表演如此之好,以至于我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是对她表演的降格。至于其他演员,我只要求他们一件事:”别演!”他们先是答应,然后开始……演。我不得不加以干预,让他们停止。片中的祖父没有这个问题,但他不是一个演员,而是一位路人。
一段时间后,我还是设法让片场沉浸在一种轻松的气氛里。因此,我们往往拍了两个小时就收工了,拍得非常快。技术团队非常喜欢我,因为我们总是比计划提前完成工作。这一切都在准备工作中:你会注意到,我从不拍摄反转镜头(contrechamp)或特写镜头。我也拒绝对演员指手画脚。我轻轻地说 “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拍摄了。我还会说:”试下……”和 “谢谢”。
我们能举个例子吗?搜查女主角的微胖的年轻女兵只在屏幕上出现了15秒,但这个角色完全立住了。你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面孔。而许多导演,包括我自己,经常会犯错。看看费里尼的电影:所有这些来自街头的面孔,它们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瞬间,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物。
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是这么做的:”你,就是你,过来过来,站这儿,我拍你,谢谢,再见!”人脸传达想法的能力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想费里尼、佩特里或奥尔米的《工作》中的演员吧。他们的面孔是如此丰富,就像一个调色板上的众多颜色。

说回这个年轻的士兵,她是我表演系的一个学生。她凭直觉、带着幽默感,在我没有给她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完成了表演。我只是给了她一根黄瓜让她啃。
祖父的角色所穿的服装是什么?
一战期间大革命前的制服。今天,西方的年轻人、甚至是俄罗斯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哥萨克人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有多激烈。在影片设定的年代,只要提到哥萨克叛乱,你就会被关进监狱。所以这套衣服是父亲给他的共产主义女儿的一个信号,让她感到害怕。
祖父对历史的态度十分悲观。他是否是你在银幕上的化身?
不,我的声音贯穿了每以个角色,甚至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理解他们每个人、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恐惧和他们面对历史事件的无力。他们的行为皆出于恐惧,这点我可以理解,即使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件好事。我们研究了纽伦堡审判中纳粹领导人的日常智力活动:他们并非天性残忍,反而个个天资聪颖。这种双重性是我在影片中阐释的观点的推动力。
这个观点比你弟弟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他的斯大林题材的电影《烈日灼人》中表达的观点要微妙得多。在《烈日灼人》中,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每个艺术家、影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于我而言,从《邮差的白夜》开始,经过《战争天堂》《罪恶》,再到这部电影,我避免做出任何草率的判断。但不评判并不意味着漠不关心。
伯格曼说过:“你只要努力,达到当下的最大强度就可以了。”但奇怪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把许多看起来至关重要的因素放在一边。这是你为了达到真相而必须摆脱的事物的最核心部分,魔法则诞生于周边的小事,这些小事则潜藏在剧本中。剧本必须保持中立,以便深入事件的核心。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好吧,我说的有点玄……但我已经83岁了,我对生活和做导演有一定的经验。这是我找到的方法,它既能把事情办成,又能把功夫都藏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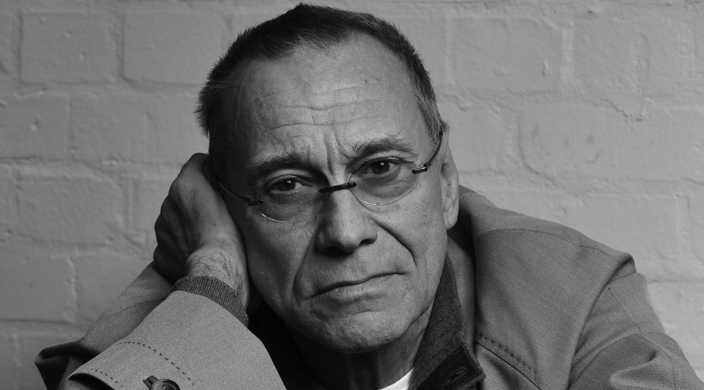
-FIN-
原文标题: Le saut quantique de la tragédie
原采访者:法比安·鲍曼Fabien Baumann 皮埃尔·艾森里奇Pierre Eisenreich
来源:《正片》Positif 第727期
翻译:小茗同学
校对&排版:小航
审稿:Xavier
文中带*处表示译者注
图片源于网络,侵删
本文仅供交流学习,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