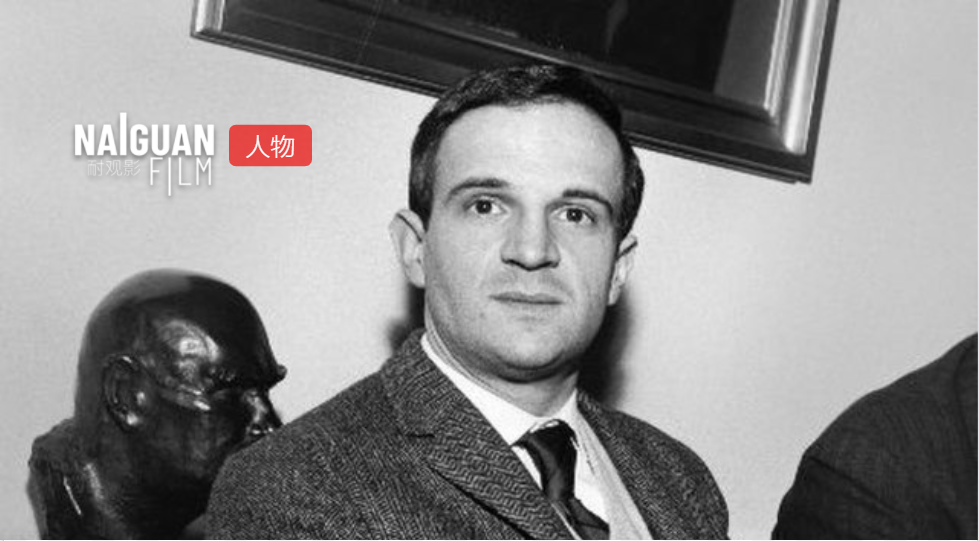
如今,重温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所有电影(不仅仅是那些出于某种原因,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国生产时期,确立了里程碑地位的电影),往往能体验到迥异的风格和参差的质量。特吕弗是新浪潮的青年电影人之一。大家对他最多的指责,就是背弃自己的原则,从评论家转向导演,投身于了他曾刻薄诋毁的电影领域;而他的一些作品,也的确没有逃脱这种偏见。还有一些作品大概受到一些严重过时的”现代性”的影响。在这些零星表象的背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能够勾勒出他大部分作品特点而又从未变过的轴心,并且注意到一种惊人的、超越那些不公的成就的连续性。这也证实了那些年轻的影评人笔下的关于电影的“作者性”的概念的优缺点。
我认为,特吕弗的前三部电影可以说是有规划的。它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风格路线,并在他之后的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得以完善,但一个不变的特点,比前面说的要创新得多,这无疑是他的作品质量不稳定的原因:愿意打破叙事原则,让节奏慢下来或加速(尤其多亏了非常精确的分镜和有趣且创意的剪辑),并利用这些意外找到自己的电影形式。

心不在焉的态度
《四百击》展现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安托万·杜瓦内尔的冒险之旅,至少存在于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中(如果抛开最后一部,《爱情狂奔》,它和其他的片子有很大的不同,我回头说)。多尼尔,作为主角,拥有把观众拖入他居住的世界的资格,也就是说,与观众分享用他的方式所看到的东西,即个人的生活时刻和人际关系,以一种不稳定的,极其私人的方式。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无论是对职业的、情感的还是家庭的规划,主人公四处游荡、随心所欲、出轨、闯祸,但这些性格和戏剧化的内容都是相对的。这无疑会影响故事的叙述方式。与情节剧或希区柯克式的悬疑叙事手法相反,如果说最终的结局给了在学校里撒谎和对婚姻不忠的少年安托万相应的惩罚,那也不是影片想强调的。正如《偷吻》结尾处的伦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多尼尔无可救药地处在临时性、短暂性的边缘,这意味着那个时期的的漫不经心和自我的存在。
得益于让·皮埃尔·里奥的非凡演绎,导演在这部”传奇故事”中找到了合适的电影基调,这无疑使它成为一个时代、一代人最贴切的肖像之一。不招摇,而是在自己的原则下默默生活。既不挑衅,也不反叛:和骠骑兵和参加过五月风暴的年轻人相反,是对各种社会环境的极端蔑视。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描绘了里奥演绎的人物行为和特吕弗故事的特点。对于后者,时间的参照和世俗的约束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当下体验到的情感,而且只在当下。没有任何强调:既不是军队,也不是劳教所,更不是家庭的拮据,《四百击》结尾的长镜头最终让多尼尔摆脱了一切压在他身上的、给他带来持久痛苦的东西。通过诺曼底海滩上那著名的镜头,我们在这个年轻人内敛的穿着下可以勉强推测出。

一个新的空间
《射杀钢琴师》整个故事都呈现了这样一种状态:不负责任的兄弟姐妹、混乱的事件、没有重点的叙事。在一次放映时,特吕弗为了捉弄观众,在一个晚上让法国电视台调换了胶片顺序,以至于叙事混乱,竟并没有人发现……但这部影片也开启了他的作品中的另一个空间:那就是不可能的、毁灭性的爱情,带有破坏性情绪的戏剧性主题。并奇特地嵌入警匪情节,但在闪回情节采用了不同的美学风格:超大景别、景深、另一种措辞……。”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无法阻止夜的到来。妮科尔·贝尔热所饰演的角色在自杀前说道:”生活很黑暗,越来越黑暗,没有出路。”特吕弗的作品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那就是,他非常重视的各种类型的混合,包括在他的许多改编作品里,尤其是侦探题材。喜剧与悲剧场面交织,精彩的运镜,玛丽·杜布瓦倒在雪地里,伴随着杀手的狂欢场面。
如果说《射杀钢琴师》的成功是因为其基调干脆,场面出人意料,故事发展别出心裁,我相信接着走这条路的电影(主要占据了二十世纪60年代的电影)并不会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嘲讽的基调已经过时了,影响往往显得毫无根据。他们之所以痛苦,正是因为他们时时想与感情保持距离;《骗婚记》中贝尔蒙多和德纳芙之间的伟大场面,或者《情杀案中案》中芬妮·亚当的高光镜头,只能艰难地在时而空洞的叙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激进的浪漫主义
第三部电影《祖与占》的故事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个时代来讲非常前卫的三人恋爱模式,按照自己的心情去生活和去爱的自由,带有爱情的友情,以及将幸福搬上荧幕的某种天赋。这些都改编自真实故事,影片中大部分剧情遵循了亨利-皮埃尔·罗谢的原著小说的内容和主旨。但《祖与占》也是一部充满激进的浪漫主义的悲剧,而这种激进的浪漫主义也将出现在特吕弗后来许多作品中。
镜头在阴沉的森林上方的大幅移动,影片中叙述者不安的嗓音,加之尤为重要的电影中人物经历的有如致命的激情般的爱情,这些都早已预示了死亡,自杀和爱情中无边无际无望的痛苦,这些手法成为电影中的亮点,且在《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和《隔墙花》中得到更好的运用。特吕弗被认为是一个温柔,善于表达内心微妙情感的导演。这在不光是这些电影,同时还有被他们的摄影指导阿曼卓斯称为“如书法般极具艺术性”的《两个英国女孩儿与欧陆》,《绿屋》一系列影片中是如何体现的呢?同样还有以葬礼开始的《痴男怨女》,我们清晰地看到相比于爱,是“爱的想法”占据了主人公的头脑。在自由主义的表层下,且尽管电影的拍摄节奏带有跳跃性,我们仍可以看到相比于所谓小说性的浪漫精神,是以强烈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来源的浪漫主义位特吕弗的作品奠定了基调,一种我们更能从谬塞而不是诺瓦利斯作品中找到的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精神,这点毫无疑问,然而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一点一点侵蚀着主人公对爱的找寻。
诚然,这些作品大多被归于特吕弗的第二部分导演史里。彼时,他的风格形象已经确立。但《祖与占》已经表现出这些特征了。这些与早期特吕弗多部电影的主人公安托万·杜瓦内尔所经历的故事截然相反,从戏剧和审美的角度都有所不同,如音乐,场景的表现力(以及后来的颜色),夜晚与内省的主义,不可避免的如机械般重复的疯狂,强迫性的痴迷的轨迹……

关于叙事方式的思考与实验
即使特吕弗所有的电影都有交叉的联系,有类似的影像、台词和故事,我们大可把其他一些片子放在一边,专注在那些采用了最激进的方式来构建故事的影片上:一边是那些杜瓦内尔,另一边是那些狂热构思的片子。一类讲述火热的故事,另一类故意谨慎地远离了这个主题。这是在这些影片中,他关于叙事方式的思考和实验得以最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也正是新浪潮导演们最大的贡献。在他们分歧最严重的时候,戈达尔说特吕弗:“我觉得弗朗索瓦根本不知道怎么拍电影……(在《四百击》之后)他除了讲故事什么都没有做。”
但他的电影恰恰不是在只讲故事:它们从未停止去探讨如何来讲故事。我们看到分镜头,打电话和线索的运用, 来自其他影片的影象的插入(这里或那里的存档,和引用自他自己的《爱情狂奔》的16分钟的影像,或许是他所做的最鲜明的最费心血的叙事联系),以及突破常规约束的并不复杂的剪辑。当时在最具创新性的法国剪辑师之列的塞西尔·德库吉斯和扬恩·德戴和特吕弗的合作并不是一个巧合:神速的书信联系(没错,在特吕弗的电影中,书信比今天的电子邮件更快)、冻结画面的独创性(马丁·斯科塞斯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参考运用这种手法)、表现性和叙述性动作的交替进行,呈现出不断被重新塑造的不同的故事的张力。
除了按照主题或者某些被重复很多次的故事分类,特吕弗的电影也是分不同的板块存在的,且这些板块自写作和体裁上不尽相同,这便是1955年电影手册刊登的文章《阿里巴巴和作者论》的作者的想法,那些认为多样性叙述对理解影片和坚持单一执念拍摄必不可少的人也抱有同样想法。
– F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