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题材一直围绕着灾难,大灾变和世界末日。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灾难总是铭刻在我们的历史中,伴随和塑造着我们的历史。我们都记得出自圣经启示录中著名的四骑士的形象,征服,战争,饥荒,死亡,这告诉我们,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尘世只是个伤心之地。毋庸置疑,在我们的记忆中,骑士确实是存在的,无论他们骑行在在虚构的故事中(《亚特兰蒂斯的消失》)还是在现实历史里(1348年的大瘟疫,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2500万人口)。
//一场无可比拟的完美灾难
这就难怪一个多世纪前,先是文学然后拍摄为电影的科幻,带着无限的局限性冲进了这个题材:此类电影关注的是想象可信的、可能的或概率的未来,科幻作为一种在一百多年里由文学拓展到电影的体裁,带着无限的可能朝着这个主题进发,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它聚焦于对一个可信的、潜在的和可能的未来的想象。因为在最好的故事里,一切并不会一帆风顺(“幸福的人没有故事”),但往往戏剧性极强,所以灾难题材作品无可避免地描绘着最糟糕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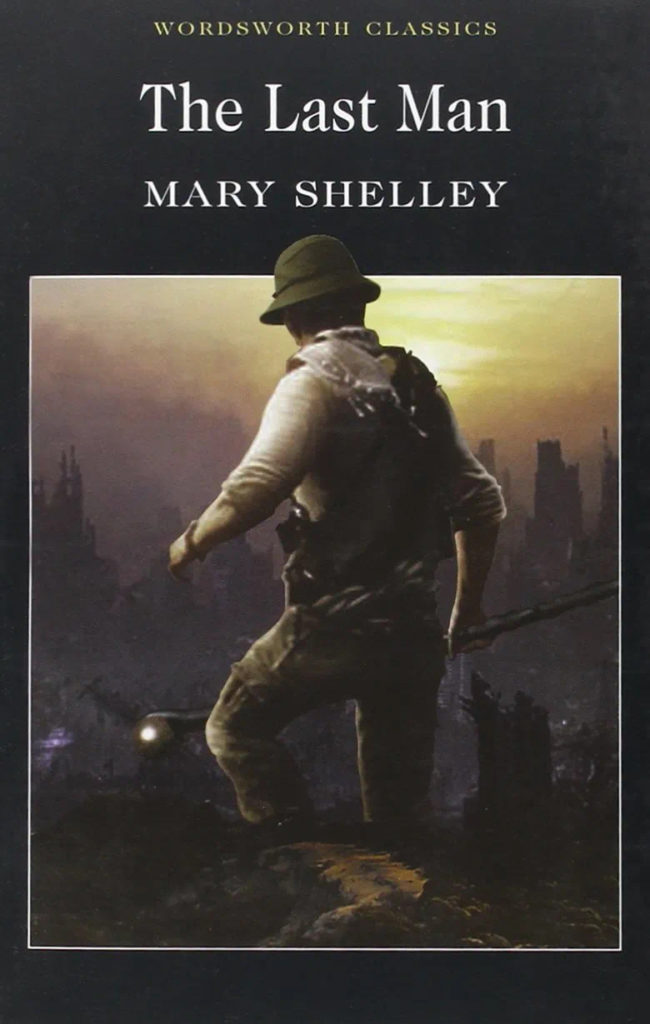
《最后的人》,1826
一场完美的灾难,少不了悬念的制造,而最常见的悬念就是:谁会死丧命,谁会脱险?如果只剩下一个人…… (参见1826年玛丽-雪莱的《最后的人》,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灾难小说)
杀死全体或者一部分人类,是一种变态的乐趣,每个科幻作家几乎毫不犹豫地沉溺其中。作为一个作者,我自己也大量借鉴了这一点(《Le Monde enfin》,《Fleuve noir》,2006年;包括广告),我经常说:当你悠闲地坐在电脑前,手边放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盘算着最坏的情况,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是放飞想象,还是在玄幻小说的调剂下,唯唯诺诺地照搬现实呢?
《奇爱博士》
至少在所谓的冷战年代,大灾变最好的一个主题就是原子弹战争。只要重读美国作家穆雷-莱恩斯特的《刺杀美国:美国作家穆雷-莱恩斯特》(1949年),或者反复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就会深信不疑。这是纯粹的想象力吗?让我们来问问广岛和长崎的日博社,这是否只是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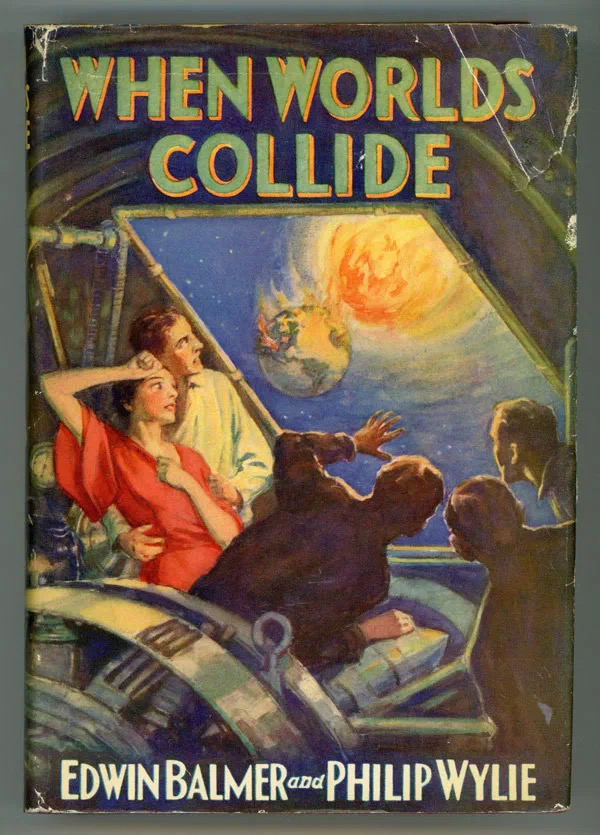
《当宇宙相撞》by Edwin Balmer,Philip Wylie
我们能举出成倍的例子,以火山学为例,记得1883年8月27日喀拉喀托火山的爆发,引起了一场海啸,死亡人数达3.6万人,引发的高空尘埃遮蔽了天空两年,远至欧洲都被波及其中。毫无疑问,只有那颗一举灭绝恐龙且被影人们拍了又拍的陨石(从根据Edwin Balmer和Philip Wylie的小说改编,Rudolph Maté在1951年再创作的Choc des mondes,到Armageddon及其衍生作品)从我们手里(再一次?)逃过一劫。
//大自然的怒火

《地狱之旅》
既然我们在看电影,那么第一部灾难片是什么时候呢?尽管这个词似乎是在70年代初出现的《地狱之旅》,但这个类型的电影与电影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早在1902年梅里爱本人就以《佩雷山爆发》(L’Eruption du mont Pelé)探讨了这个问题。
其实,灾难片这个概念本身,即荧幕上上演的一部部越来越恐怖的故事,只是人类最古老的恐惧的具象化:面对自然的愤怒,甚至被自然打败。其实,灾难片这个概念本身,即荧幕上上演的一部部越来越恐怖的故事,只是人类最古老的恐惧的具象化:面对自然的愤怒,甚至被自然打败。

维苏威火山
地震、火山喷发、潮汐、飓风(巴斯特-基顿试图用投掷石块的方式来对抗其中的一种)是造成这些灾难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大灾难中的每一个会让那些不幸的卷入者感受到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于庞贝的6.5万居民来说,维苏威火山的喷发确实是世界末日,他们那个世界的末日。
末日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不管以什么方式,它总有一天都会到来。用墨菲的著名定律来概括就是:任何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是: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不可能选择自我毁灭。然而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人类正以其自身的破坏性成为各种灭绝的主要媒介和罪魁祸首,随着第六次灭绝而宣告并成为现实。而我们的灭绝将发生于何时何处?也许具象得体现在2020年现行的大流行病冠状病毒的突然袭击?
基于天性里的自我毁灭性,人类将是导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里各种灾难的主要因素和罪魁祸首,这会是我们的灭绝。在此前提下,我们该如何处理像2020年突袭全球的新馆病毒这样的疫情类主题?
// 势如闪电
这可能有些反常,虽然病毒灾难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刻画,主要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黄祸论”(注:欧洲殖民帝国与美国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与日本具有批判性的代表用语)和对 “德国鬼子”(注:法国士兵对德国士兵的称呼)的仇恨孕育了许多关于德国或中国实验室培养致命病毒的故事,但这个主题很久以后才被第七艺术(即电影艺术)所呈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忽略一些萌芽期的作品,例如大卫·克伦伯格的《狂犬病》,它只涉及了一些被感染的个例。
第一个拍摄此主题的作品是《极度恐慌》(沃尔夫冈·彼得森,1995年),在该片中,扎伊尔的一个小村庄爆发了一种来源不明的传染病,蔓延至美国前的48小时内死亡率达到了100%。它是科幻作品吗?当然,部分情节是的,例如使用原子武器对病毒蔓延的城市进行消毒的假想,但就故事的基础而言,1976年发现的埃博拉病毒,至今仍持续造成数千人死亡,就可作为它的原型。
《复活之日》,1980
当然,《复活之日》(深作欣二,1980年)比它更早,但那些病毒来自于从美国偷来的细菌武器,并在一次普通的飞机失事后失控传播,因此,它更多的是政治意味,我们可以断然定义为:美国佬还没有破坏一切。
《流感》,2013
《流感》(金成洙,2013)中,有另一种病毒以闪电般的速度在首尔蔓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和死亡,并且更符合我们对流行病的认知。随着这种变异禽流感的蔓延,受害者大规模地咯血和死亡,而政府却无法为面临威胁的居民提供任何药物或疫苗。
《传染病》,2011
本片之前还有《传染病》(史蒂文·索德伯格,2011年),2020年再看这部电影,许多电影观众都会惊讶于它与时事的惊人吻合:路人戴着口罩上街,食品店被抢购一空,警察封锁了道路,室内体育场被征用来安置病人,过量的尸体被埋在乱葬岗,军队分配食物……这是对当下状况的精准预测?不,因为如果你想拍摄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只需回首借鉴一下历史就足够了。
// 病毒会从哪里来?
正因为有了这个标志性的样本,我们可以看到,给这个主题赋予科幻色彩,或者追求一种超越简单纪录片形式的原创性是多么困难。为了丰富剧情,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探讨:病毒会从哪里来?
《人间大浩劫》,1971
没错!比如《人间大浩劫》(罗伯特·怀斯,1971年),改编自迈克尔·克莱顿两年前出版的小说《天外来菌》,故事开始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附近,美国的一枚太空探测器带回了一种毒性极强的病毒,可以摧毁它周围的所有生命。更有甚者,在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最著名的作品《有谁去那里》(Who Goes There?,1938)中,病毒可以在极地冰层下,一个飞碟坠毁的变异生物体内休眠5万年。无论它是否因为其载体的意外挖出而醒来,它都可以通过血液从一个身体传递到另一个身体。
《怪形》,1982
约翰·卡朋特在《怪形》(1982)对艾滋病的隐喻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这次敌人终于可见,而不是一直藏匿在我们的细胞中。
病毒也可以在军事实验室制造并逃逸,例如斯蒂芬·金的小说《末日逼近》(1977),米克·加里斯在1994年将其改编为6个小时的电视迷你剧,剧中为了表现生存之战,传统意义上的流行病主题很快被抛弃,各种游荡的帮派为了争夺剩下的世界的霸权而相互对抗。
《十二只猴子》,1995
更有趣的是,《十二只猴子》(特瑞·吉列姆,1995年)从克里斯·马克的《堤》中获得灵感,并脱离了它的主要方向:迫使幸存者生活在地下的不是核战争,而是一场据说是由一个极端的环保组织 “十二只猴子军 “引发的大流行病。实际上,这种恐怖分子的个人行为使我们陷入了一种不光理论上可行,还可以付诸行动的事实中,如果我们还记得1995年3月在东京地铁里发生的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即使它是化学而不是生物意义上的。
不得不说,创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流行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好医生科诺克(注:好医生科诺克是法国戏剧代表作《Knock or the Triumph of Medical Art》的主人公)所说的,健康是介于两种疾病之间的暂时状态。
我们是否还记得,就法国而言,1969年的香港流感导致31000人死亡?等待我们的大型灾难,相比遇到威尔斯的火星人或者哥斯拉大街拐角处的丧尸群,更有可能是冠状病毒(SARS-CoV-2)或它的变种,并且,对它们而言,M16突击步枪的扫射是无效的。
因此,永远看不见的敌人引起的恐惧,出其不意地袭击着我们,其无形的存在只会使编剧和导演不断认同希区柯克所阐述的,恐惧越强烈,电影越好。
我们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几年里,关于这个题材的科幻电影会成倍增加,预想带来的可怕缺点是,它们经常在背后预测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其余的人,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坚定地等待着它们。
FIN

